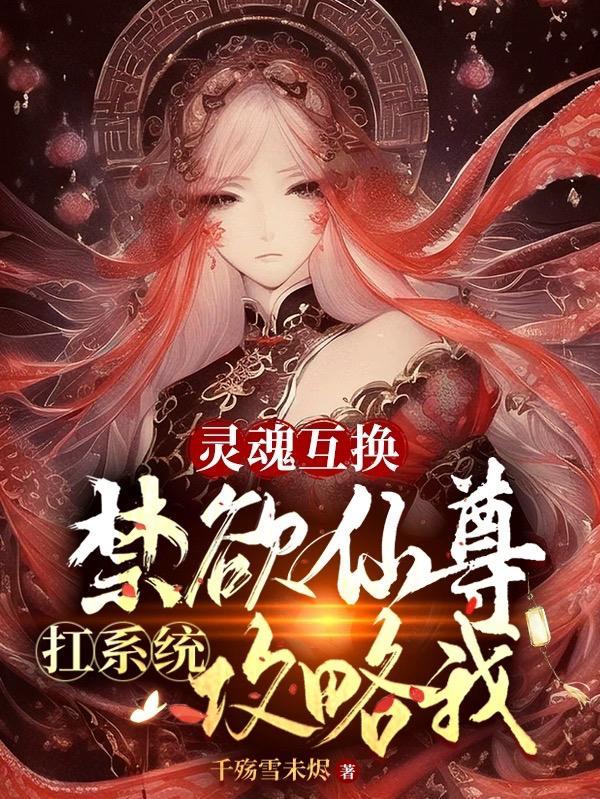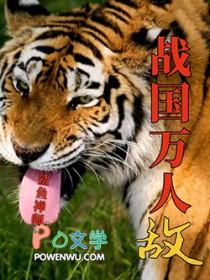乡村文学>殿下他好像不行 > 第171章(第1页)
第171章(第1页)
文妃赶紧屈膝行礼:“殿下……不,陛下此话从何说起,妾身一直感念陛下猎场中救下意儿性命,也在佛前发愿,若能报答陛下恩情,万死不辞;但妾身微薄卑微,何曾能够相助陛下。”
“为时尚早。”萧彦抬手制止她这个称呼,也不挑明,只道:“本王府上医师制的两瓶烫伤药膏,明日命人送来。”
文妃一滞,继而坦然拜谢:“多谢殿下明察体恤。”
与聪明人说话很是省力。萧彦笑笑,示意她留在此处照看萧意,自己往正殿行去。
前日滴血验亲之时,文妃乱中趁人不备,将榻尾取暖的一个汤婆子藏在衣下,拉回萧意后,虽未触碰,自己却借机靠近那白瓮,袖中高温热流传向瓮边,水面未动,水下却微起暗涌——两滴血因此迅速相融。
不想文妃虽孱弱,却胆大心细,在场的人除了萧意,均未发现她的小动作。就连当时离的最近的萧彦,也因紧张而未觉一旁温度的细微变化。
只是在回銮启程时,萧意悄悄来寻他:“二哥,我母妃手臂起了好些水泡,可她不让我告诉别人,也不让找御医。”
——萧彦细一回想,方才察觉。
那时萧意在猎场遇险,救他不过是萧彦顺手而为,并未放在心上,文妃已然道谢,不料想她看似柔弱、实则刚强,敢在众目睽睽的紧要当口行此险招帮他。
谢承泽得知,点评道:“种善因,得善果——殿下纯善,这是应得的。”
萧彦失笑——他两世的所作所为,何曾与“纯善”一词沾边。
但文妃的冒死相助确是他意料之外——对于人心,他萧彦惯于评估、收买、拉拢、谋算,从未想过有人居然不经吩咐指使而自发相助。
这感觉如何形容,仿佛冬日熬尽、种子自冻土之下醒来——似乎与他无关,但又令他心情不坏。
皇帝崩殂,四方云板叩击,回荡在空阔宫墙内外,惊起一阵夜眠的鸟。
萧彦独自行走在廊下月影中,驻足,仰头望去——所有的鸟都已划过这浓浓夜色,毫无痕迹。
推开殿门,闻讯赶来的满满一殿诸人:皇后,萧竟,皇室宗亲,礼部官员,一齐望来,随即向他跪拜:“陛下万岁!”
这是前世他梦寐以求的时刻。
尽管此刻心情复杂,萧彦仍然站定,伸手,平缓道:“诸位请起——”
圆满
虽是仓促登基,但处理政事萧彦早已得心应手,并不局促。君位更替,确有波澜,而兵部刑部已明确支持,萧彦以雷霆手段清除异己,拔擢寒门人才,不下半年,羽翼速成。
时已入夏,傍晚时分,乐孟递来一封信笺。
信纸宣透,隐有海浪纹理。
“七海五江乘长风——”萧彦默念。
两世之中,亦万重都鼎力支持了他,理应得到他的回报;可展信看时,却不过是几行致敬之语,并无他话。
这个人令他看不透,却也不愿深究。
正思忖间,良太妃施施然前来:“福宁的嫁妆单子,陛下可瞧过了?母亲总觉得太过奢侈。”
斜阳落下屋脊,萧彦估摸谢承泽快到了,只想赶快了结话题:“阿晴的嫁妆朕已定了,不过略比祖制常规多了些,而刘家对朕拥立有功,正是相宜得当。”
良太妃一笑:“母亲知道你的性子,向来说一不二,如此就依陛下所言。眼下国丧未过,福宁年纪还小,此事并不着急。可是陛下自己的事,母亲却不得不多说几句。”
萧彦闻言,整装危坐。
良妃接着道:“大行皇帝本已子嗣不多,致使宗亲不旺;可如今你宫中连个人都没有,何时才能得子嗣……”
萧彦早料到她要说这些,挥退殿上宫人,忽然岔开话题,直截了当道:“请问母亲,朕是否是先帝子嗣?”
“咣当——”良妃猝不及防,手中茶盏翻倒,大惊失色:“你——”
萧彦观其神色,若无其事地笑道:“母亲勿慌,当日滴血验亲,朕确是先帝血脉,朕不过玩笑而已。”
“可笑如先帝那般手段缜密,也难保子嗣是否亲生。母亲知道朕不喜女色,若为子嗣而勉强填充后宫,恐怕今后更是难保皇室血脉纯正。”萧彦说完,不耐起身,隐含逐客之意。
茶水打湿华贵衣裙,良太妃一脸难言地看看自己儿子,匆匆离去。
谢承泽后脚就到了,应是自军中赶来,虽身着箭袖常服,手上引弓扳指却忘摘下。他首先装模作样地拜谢:“陛下厚赏抚恤郊营眷属,承泽感激。”
抬眼见他眉眼中犹自烦郁未消,忙上前来抱住:“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萧彦恨恨道:“你明明已嫁与我,可我搬进这鬼地方,处处是规矩、人人都算计;你倒留在我的府邸,带着你那俩孩子和狗,无人管束,逍遥快活——”
谢承泽先是轻笑:“那你倒是册封我为后啊,承泽自然愿意入宫,朝夕伴圣。可你狠心,不给我锦衣玉食,却将我扔回军中——”
继而声音凝重:“天气暑热,南境连日阴雨泛滥,军中才开始备战伐雍,却刚传来消息:南境瘟疫蔓延。若情况不见好转,只怕得动用你的御医——”
如同前世一样,南军起了瘟疫。
萧彦算算时日,随即召来顾行远:“明日启程,赶去南境,救军民于水火。”
顾行远略一犹豫,仍然行礼领命。
不待萧彦发问,谢承泽答道:“林先生的病,近日总未见起色,只怕离不了顾先生日常照看;且此去总得小半年……”
顾行远连忙摇头:“不,文举他早已嘱咐过,我当唯陛下命令是从,以大局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