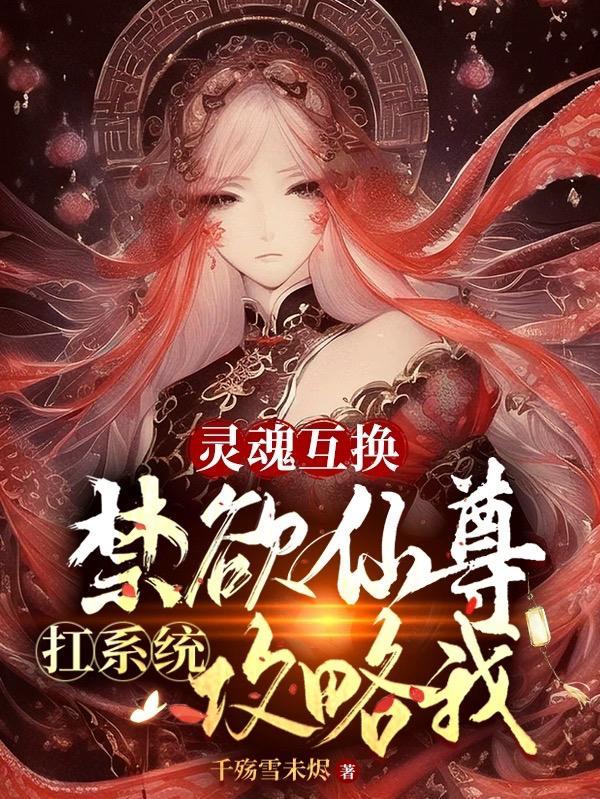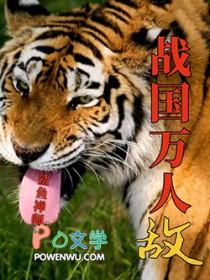乡村文学>殿下不好当 > 第96章(第1页)
第96章(第1页)
来的到底是谁,值得他们下如此血本?
萧彦隐约有种不祥预感,定睛向战船望去——
夜色中,旌旗鼓足江风而舞,立在船头的青年身着软甲,侧身弯弓,目光凛冽如星辰。隔着水面敌船,恰逢上他的视线,随即似乎微微露齿一笑,仿佛在说:殿下别怕。
谢家最杰出的子弟、南军默认的下一代接班人——才是水匪今夜要围剿的对象。
今夜本是他萧彦以身为饵,给戴氏等一众仇家布的圈套;却被有人将计就计,反而利用他引谢承泽进入围杀陷阱。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萧彦啊萧彦,你已重活一次,为何仍总是败于人手?——萧彦面上不显,广袖之下暗自握拳。
林文举随之看去,拍着船舷叹道:“怎么来的是谢小将军?!他不是受伤未愈么?”
自然是他知晓了谢栋与自己的暗中约定,主动要求前来——他连不相干的人都愿舍身去救,保护爱人安全更是会冲在最前面。
——承泽啊。萧彦闭目,摒住眼中泛起的微微湿意。
林文举着急道:“情形不对,该想办法警示谢小将军才是!”
但现下风声、雨声、浪潮声,以及各方人员的呼喝声,充盈耳膜,何种信号能传达陷阱之意?
却见萧彦重新睁开双眼,已然恢复一贯的深邃冷静:“升起风帆。”
“啊?”林文举一愣:“眼下的风向,若扬帆岂不是离港更远?”
不容他置疑,身后的乐孟已干脆应命:“是!”——拧身便利索爬上桅杆。
不多时,风帆升起,船身随之移动,底舱许是被水浸泡,不知何处轧轧作响。
正全速赶来的两艘战船果然放慢了航速。
林文举恍然大悟:“对啊,此时展开风帆示警,他们便能知晓有反常情况!”
“对什么对,”顾行远不知何时收好了那截断腿,凑在旁边,苦脸嘟囔:“援军察觉陷阱,一转身走了,剩下咱们怎么办?!你没发现,船已下沉了五六尺嘛!”
林文举难得没骂他,陷入沉默。
江面广阔,雨打湿衣衫。两边魏船都挂着蚌壳防风灯,两团暖光之间隔着浓重的黑暗,与密密麻麻的匪船。
萧彦长身玉立,一直望向谢承泽。喊杀声中,明明暗暗的光影里,他知道谢承泽也正眼也不眨地望着自己。
林文举看在眼里,明知本不该打扰,但见萧彦再也无话,终于忍不住提醒道:“王爷,谢小将军那边看来已经知晓咱们示警,现在是不是该把帆再度收起?”
顾行远也跟着附和:“是啊,免得被吹到江心,下沉更快。”
萧彦却抬手:“不必。”
乐季得令,在舷边指挥□□手:“待靠近些,借亮瞄准再发箭!”
林文举渐已摸清主上脾气,此时虽急惑不解,却按捺住嘴,不再置疑。
顾行远却不懂,大呼小叫:“这怎生是好?不收帆,待下一拨援军来,咱们已经沉在江心了!这,在下不会水啊!乐都卫,你给劝劝,哎——”
乐孟从桅杆滑下,不等萧彦吩咐,熟练地将顾行远拖回房内,按在座椅上:“您先歇会,要是无聊就研究研究这腿,喏。”
顾行远捧着那截断腿,看乐孟站回萧彦身后的背影,不由嘀咕:“一群疯子么这是。”
但见林文举纤瘦身影也镇定立在萧彦旁边,又觉没那么害怕了:沉便沉,横竖和他在一块。顾行远定下心神,拿布擦擦这断腿,仔细察看起来。
反杀
已至深夜,雨势减弱,风仍撑满帆布。
底舱水深渐没至腰间,而船继续向江心漂移。匪船钉来的钩绳本是绷直,很快弯坠——他们迅速接近匪船,船舷边的人已经能看清匪船上的桨。进入射程,弩箭命中率大大提高。水匪不曾料想被突袭的对象不但不逃反而开始靠近,慌乱间分出人手纷纷回箭。
乐孟提醒萧彦:“流矢纷乱,殿下请进内暂避,外面交与我们即可。”
萧彦摇头,他要亲自指挥,且要等着与谢承泽相见:“文举进去吧。”
这场面林文举从未经历,要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但战场对男人天生有种吸引力,同时他更好奇萧彦的策略,于是也拱手拒绝:“文举请求观战,不给王爷添乱。”
匪船上人摸不清这边状况,依然按照之前定好的方略,团团围住谢承泽的船,齐齐搬出火油,蘸在箭头,点火往战船射去。
风灯之下,只见谢承泽做个手势,似是示意按兵不动,船上士兵只是兜水灭火。跟随其后的另一艘战船随即加速赶上,拉开间距与打头战船并排而行。
见没有反击,水匪愈发嚣张,渐渐都凑到上风口,对着战船集中攻击。开始只有零星几点落在甲板,渐渐战船舰楼上也钉了着火的箭。
越来越近,火光中,两人终于看清彼此脸庞。
挎弓青年临危不乱,对副将作出的指挥手势利落沉稳;只有在得空望过来的间隙,眼中流露无限柔情。
来南军没多久,他已能独当一面了,果然是能成为天下第一将的人物。萧彦想起前世,有些可惜自己前世从未见过谢承泽在战场上的风采。
随行战船缓慢调整航向。林文举这下终于看得明白,兴奋道:“王爷妙计,真让文举眼界大开!”
两艘战船似乎出发仓促,没带足箭羽,一轮一轮地反击,却成效不大。
箭矢往来中,所有匪船都铆足劲追着大船,忽有水匪放箭时转头观察四周,意识到不妙:“当家快看,官军把咱们围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