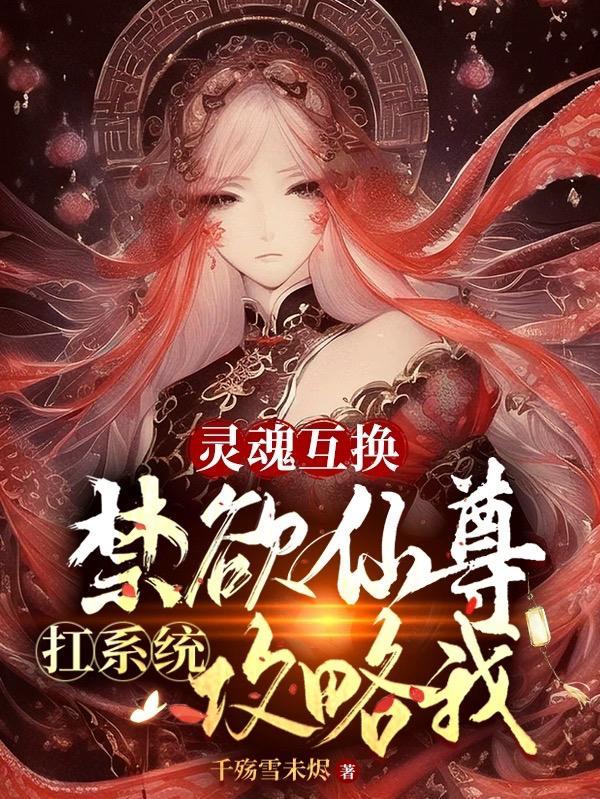乡村文学>丞相大人金安 > 第28章(第1页)
第28章(第1页)
“阿芙,是我对不起你,南舟的死,都怪我。”
苏母脸上没有泪痕,她的泪早在前几天就流干了,只是平静,却因过度的劳累而显得有气无力:“不怪你,这是他自愿的,当年亦扬死的时候,他就说过,总有一天会轮到他的,他心甘情愿。”
先帝背对着他,看不清表情,一身玄色大氅,衣着极素,作为帝王,他是不需要为一个臣子守灵的,但此时的发间,却是连一顶玉冠都没有,只用玉色的发带半束着。
“为了这件事,阿松死了,亦扬死了,南舟也死了,他们都走了。”他的声音里透出无尽的隐忍与疲惫,因为长期的咳嗽而嗓音嘶哑:“阿芙,他们都是为我死的。”
苏母本来委顿地跪在蒲团上的身子突然一震,她转头看向先帝,缓缓从地上爬起来,因为跪得太久,身体甚至有些摇摇晃晃,先帝连忙扶住了她。
这个时候,他才看到先帝的侧脸,灵堂的烛火被风吹得摇曳,光影晃动间,那是极其苍白的一张脸,他和苏母是一母双胎,两人长得极像,而此时同样的憔悴不堪。
“南舟从未后悔过,亦扬也没有,我相信松哥也没有。”苏母紧紧抓着先帝的胳膊:“陛下,我也从未后悔。”
苏岑说到这里,面色渐渐冷下来:“我去问过贺瑜,连他也不知道那件事具体是指什么,现如今,可能唯一知道当年真像的,只有一个人了。”
太皇太后。
是什么让苏南舟甘愿抛下妻儿赴死?又有什么是贺瑜作为一国之君也不可晓的秘密?
裴决也陷入了沉思。
这时,外头苏浩的声音传来:“小候爷,小王那边传话来,说亥时过来。”
裴决回过神来,问苏岑:“有消息?”
苏岑听到声音只“哦”了一声,听到裴决问,想了想才说:“应该是吧。”
说完,他又看向裴决,这时的裴大人已经又回到了公事公办的冷脸——苏岑最不喜欢的这张脸。
他目光一转,落到了上午碰过的地方——裴决此时耳垂已经恢复正常了,阳光下暖暖的白,绒绒的很软的样子。
苏岑想到今天在小隔间里他失控的样子,觉得那样才好看,开口道:“小王是贺瑜,今晚他会过来。”
……天子是这么称呼的吗?为什么是小王?
苏岑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笑嘻嘻地道:“他不是君王吗?我就叫他小王。”
贺瑜对苏岑的宠爱已经到了一种完全没大没小的状态,苏岑对他的称呼多的不得了,有时候好点就直呼其名,叫他的表字,有时候闯祸了就表哥,瑜哥哥,好哥哥地乱叫,传消息就称他小王。
“他小时候胆子小,七八岁了还不敢一个人睡,太皇太后又不放心别人,就叫我去陪他睡,我就笑他,说他是王,还不敢一个人睡,胆子这么小,只能叫小王。”
贺瑜本来不想答应的,但是除了苏岑,他找不到人陪他睡,那些宫人是决不可能的,太皇太后看得很严,先帝是从来不会陪他睡的,于是只能勉强答应下来,到后来长大了,苏岑明着不叫,暗地里还依旧这么叫,他也懒得纠正了,毕竟谁也不可能想到小王会是他,这样一来,反而安全。
裴决一向难得有大的情绪和表情,哪怕有,外人也看不出来,但此时,苏岑却清楚地查觉到了他脸上表情的微妙变化。
这点变化让他心情更加愉悦,身子也慢慢地朝着裴决那边靠过去了:“我不认床,哪天要是裴大人怕黑了,我也乐意去给裴大人暖床,一回生二回熟,毕竟也睡过两回了,那床榻想必也认得我。”
裴决眼底微微一暗,说道:“这候府都是小候爷的,更何况一张床榻?小候爷若是喜欢那张床榻,让人搬过来便是。”
苏岑笑了:“我喜欢的可不是那张床榻……”
他闪电般地出手,却仍然在碰到那软肉前被人抓住,微微有些遗憾地挣了一下,却发现那手如铁箍一般,挣脱不开。
“小候爷若是因为和陛下过于亲近而习惯了这样的动作,还是不要在我身上试验为好。”裴决的眼珠很黑,微蹙着眉,让眼睛的线条拉长,更显得锋利,透出一股不悦,他擒着他手腕,微微侧过脸来:“这是僭越,我不喜欢。”
苏岑又挣了一下,却发现他力道变得更重了,莫名的不服输的那股劲又上来了:“裴相好大的脸,竟然敢把自己和天子比,这难道不是僭越吗?”
裴决脸一木,松了手,聊到这里,今日想要了解的事已经差不多了,再多的,他也不想再聊下去,站起身来:“小候爷说得有理,我先回藏锋院,不打扰小候爷了。”
虽然裴决出流岚院时已经恢复了那张冷淡的脸,可小陵仍然查觉到了他的不悦,心道这小候爷果然就是来克公子的,没哪次从他身边出来,公子能高兴点儿。
亥时前一刻,贺瑜到了候府,府里的人都已经习惯了,直接将他引到了流岚院,苏岑正躺在摇椅上晃着,见到他进来,只随意地瞥了一眼:“糖呢?”
贺瑜也没有天子的架子,对他这样子早就见怪不怪了,连披风都未取下,先从袖子里拿出一包糖来送到他手上:“太奶奶也爱吃这琉璃糖,留了一点给太奶奶,剩下的都在这儿了。”
这是从波斯那边送来的一种糖,色彩鲜艳,透如琉璃,就是容易碎,一碎了就容易化,化开了味道就没那么好了,每次送到朝中,能完好的就不多,苏岑就会让贺瑜替他留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