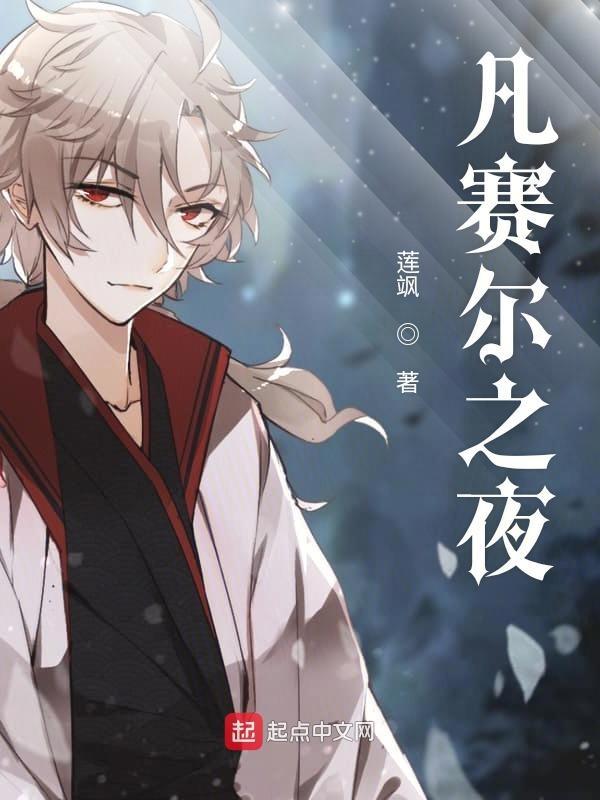乡村文学>伪装大佬那些年百度txt > 第79节(第1页)
第79节(第1页)
比病房里药味更令人窒息的,是在仪器运转的嗡鸣声中无声无息蔓延开的衰败死气。这栋楼里所有人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倒计时。
“癌症晚期的病人往往都很疼。”虚影说,“疼的受不了的时候,医生们会给他们上镇痛的药物。剂量越来越大,效果也越来越差。”
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任何一个人,只是他身体里不断溢散出光点落入到病房里的人身上,他们紧皱的眉会微微舒展,有些人的呻吟声也会渐渐低下去,难得地陷入几分钟的沉睡。
“医院里的镇痛药物有很多,杜冷丁、地佐辛、吗啡、美沙酮、芬太尼……”虚影缓慢地报着一个个令人陌生的药物名称,“但无论什么药,都不能阻止人走向死亡。”
病人的身影倒映在他白色的瞳孔里,他脸上神色怅然,竟有种悲悯的神性。
虞荼没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虚影。
虚影好像也不是要他说出什么感受,做出什么评价,他只是在做一件很简单也很纯粹的事———带着虞荼看一看。
他们离开了一楼,没有坐电梯,而是爬楼梯往上走,楼梯间里隔一段距离便能看到一个简陋的地铺,棉被上铺着床单,放着枕头,随意堆成一团的被子上搁着饼干和水壶,有的铺盖干净,有的铺盖很脏。许多人生活的痕迹聚在一起,即使楼梯间通风状况良好,也依旧有股难闻的味道。
二楼和一楼的状况差不多,三楼的楼梯间里,他们听到了哭声。
有人蹲在楼道里,刚刚挂断了电话,抱着脑袋咬着嘴唇,死死压抑着痛哭的声音,那种小声压抑的绝望甚至让人模糊了性别,好像是许许多多个曾在楼梯间里哭泣过的身影重叠在此刻。
“躺在医院里治疗的,都是家人砸锅卖铁也不愿意放弃的。”虚影说,“有的人倾家荡产,却人财两空。”
他们在这栋楼里呆了几个小时,却见到了许多场景,有病人的呼吸在这一刻停止,与世长辞;有病人的情况恶化,被推进抢救室;有人日复一日地交着天价的治疗费,最后被账单压垮;有人在轻描淡写的聊天中,选择了放弃后续治疗出院回家……
医院是人世间最痛苦的缩影。
“我最不喜欢这栋楼。”虚影说,“但我没有任何办法。”
它是生和死之间的交界线,是希望与绝望的合集。
“整整十八年,没有人能看到我的存在,也没人能听到我的声音。”他说,“谢谢你。”
在ECOM附近对视上的时候,虚影以为只是一个巧合,直到病床前,这个神秘人精准地抓住了他的手腕,阻止了他救人的动作。
十八年来,第一次有人能触碰到他。
原来人的体温……是热的。
他本来以为拉着人四处走会被拒绝,会被疑问,他也准备好了解释,却没想到被无声地纵容。
他们在医院里走的时候,他碎碎念的时候,一转头就能看到有人跟在他旁边,虽然没说话,但总觉得他有在认真听,认真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好像他们是阔别许久的朋友,只是今日才见面。
他喜欢这种感觉。
虚影说:“你没什么要问我的吗?”
他看到面前这个容貌过分俊秀、看起来很年轻的人沉默了一会:“……你的名字?”
说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虞荼其实慌了一下,但询问对方名字,应该是正常的社交礼仪吧?刚刚他在那里说了这么多虞荼没有回答,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称呼,总觉得“你”不太礼貌,“您”又太怪异。
直到虚影短暂地停下来,并反向发出疑问,虞荼才见缝插针地将自己的问题问出。
“问名字不问身份……”虚影露出一个浅浅的笑,“我的来历,你应该早就看出来了吧?”
虞·其实头脑一片空白·荼:“……嗯?”
“我没有名字。”虚影的面上有点苦恼,“我想想……不如———”
他说:“你叫我‘藏生’吧。”
很久很久之前,他这样称呼他自己。
*
“人呢??!”虞荼从宿舍的沙发上猛地坐直,脸上的表情堪称怀疑人生,“怎么又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