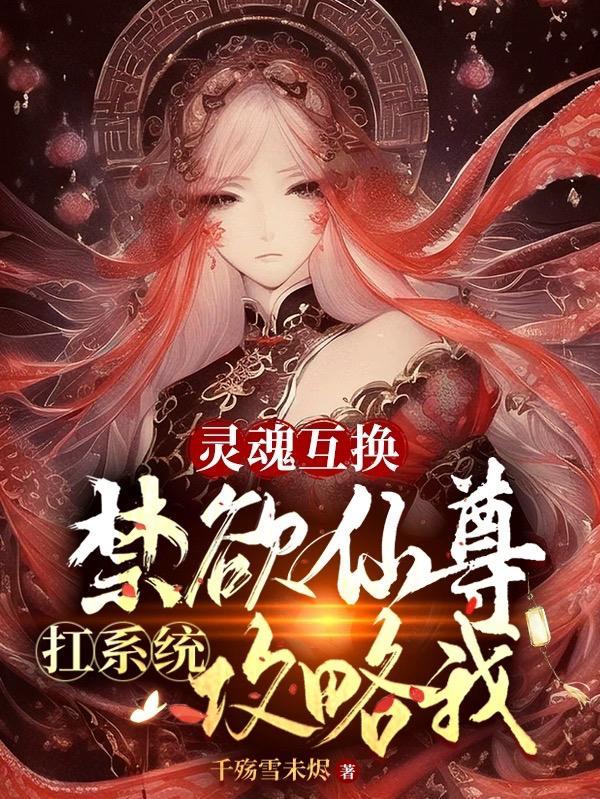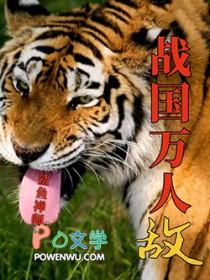乡村文学>夫君不咋的 知乎 > 第62章(第1页)
第62章(第1页)
可他们关系再不好,也犯不着打的这般狠。
两人急匆匆跑进去时,裴清川已经背脊挺直的站在祠堂门槛边。
雨雾中,青年眉目森冷,他唇色有些发白,两颊的手掌印清清楚楚,面上没什么表情。
一手轻扶在门框边,另一只手垂着,鲜血滴滴答答的顺着他的左侧袖子滴落在地上。
昨日官家微服私访,出了宫一趟,此事本就是临时起意,也没想到处声张,因此官家身边并未带多少人,裴清川自然是其中一个。
原本一切都是顺利,只是在傍晚回宫时,在京郊官家的马受了惊,裴清川离他最近,急忙驱马奔去救人。
乡间小路纵横交错,此时又是麦子成熟时,田垄之上休息劳作的人不在少数,加之那一片地种了许多玉米,遮挡视线又使得马儿难行。
裴清川与景征二人合力,才拦住受惊的马,将官家救了下来。只是小路砂砾多,他又顾着护人,不慎将手臂伤到了。
伤口不大,是被路边长了刺的树枝深深地划过,昨夜才结了痂,稍有不慎动作大些便会撕裂开,又渗出血。
今夜定然是他行动间没顾及,疤又裂开了。
寸识瞥了一眼他滴着血的胳膊,担忧道:“郎君。”
裴清川掀起眼皮看了两人一眼,说了声没事,随即迈出门槛越过二人朝外走去。
两人急忙让开路,抬眼间面色又是一变。今夜在见侯爷侯夫人之前,裴清川是特地去换了身行头才赶过去的。
而如今,青年的后背那件才换的品月色的直裰上布满了血迹,肩头那里的颜色更深,布料甚至有了破损的迹象,一道道伤痕是很明显的棍棒伤。
这是多大的仇怨,亲生母子何至于下此狠手。
两人沉默地跟在他身后,雨慢了些,淅淅沥沥的洗刷着花叶上的尘埃。
廊檐上的水痕许久才滴下一滴,院里几声清脆的鸟啼,飞鸟掠过开的正艳的榴花,惊落花瓣上盛的雨水。
夜凉如水,主仆三人静静地行在游廊上。
快到院里时,裴清川忽然开口,声音是一贯的温和:“今夜给昭昭的果子送去了吗?”
寸识一愣,连连点头:“送去了。”说完,他又补充说,“早晨郎君吩咐女使给闻姑娘送衣服,也送到了。”
裴清川轻“嗯”了一声,再没做声。
寸识正琢磨着要去找些金疮药时,裴清川又问:“那她可有说什么?”
“闻姑娘让您保重身子,记得添衣。”
裴清川想着她说这话时的神情,眼底也盛了几分笑意。
……
第二日仍是个阴天,乌云压的很低,笼罩在整个京城之上。
早朝,官家问了几句江浙的洪灾,又有几名官员禀了几道推行新政后各地的变化之类的事,朝上再无人说话。
官家挥挥手:“退朝。”
他撑着龙椅两侧扶手正欲起身,这时殿中忽有人站了出来:“陛下,臣有要事要奏。”
官家又坐稳,看着殿下的人。
那人一身绿色官服,跪在地上,垂着脑袋肃声道:“陛下,云辉将军裴小侯爷裴清川,仗势欺人,谴亲信于祁州一带胡作非为,掠夺当地富商财产据为己有。苦主状告至当地县衙处,谁料官官相护,裴大人与新上任的祁州知州沈彦相识,不仅将富商压入大牢,更是将那小县令押了进去。”
裴清川眉头紧蹙,看向跪在殿中的人。此人乃朝散大夫霍颉,已至中年,清流文官,在朝中官职不高不低,素日里谦虚谨慎,是最会明哲保身之人。
自己不曾同他打过什么交道,记得他,还是因为之前兄长极为喜爱他的字,曾在他面前提过几回这人。
霍颉怎么会知道云安县一事。
随着他的话落,朝中起了一阵低低的交谈声,有人反驳他说裴清川是忠臣,是他诬赖。
“霍大人说笑了,裴将军乃侯府出身,你所说的富商,仅为一县之富商,小侯爷还不至于贪这点财。”
“正是,臣倒是听闻,祁州贫寒,沈大人过去之后查出许多贪官污吏。”
“沈大人清廉,这京城谁人不知,霍大人却说他同裴将军贪财,简直荒谬!”
“此言差矣,人不可貌相,且那祁州离我京城相隔千里,山高水远的。你我没去过,但裴将军去过,我们不知那富商究竟是多大的富商,可裴将军知道。”
……
正争论着,忽听霍颉又道:“陛下,年初祁州有匪做乱,陛下特地派遣裴将军去了平叛,臣听闻裴将军并未将所有匪徒悉数交予当地官府。”
话落,又激起一阵喧哗。
“此事与将军有何干系,霍大人一直待在京城,难不成还比我们这一同随将军去的人更清楚吗?”
“陛下明鉴,此事乃孟序秋之疏忽,与裴将军无关。”
霍颉看着那几个七嘴八舌的替裴清川说话的武官,道:“当年裴将军的兄长便是不听劝阻,最终致使多少忠骨埋在旬途关。而今,诸位大人又是如此唯裴将军马首是瞻,难不成在诸位眼中,裴将军便是圣人,不会出一点错吗?
为官者,为国为民。如今有了冤情,诸位不听苦主陈情,反倒处处替裴将军说话,到底是存了什么心思。
下官知道裴将军素来心有成算,可那祁州离皇城远,若是裴将军真想做些什么,谁又能说的准。”
他声量高,说话间言语激动,唇下胡子都一抖一抖的。
殿内静了片刻,这时袁二爷站出来,手执笏板,严肃道:“霍大人慎言,长宁候府几代人埋在边关,其心天地日月可鉴。祁州匪徒为非作歹,烧杀掳掠,大人何至于将盆脏水往忠臣身上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