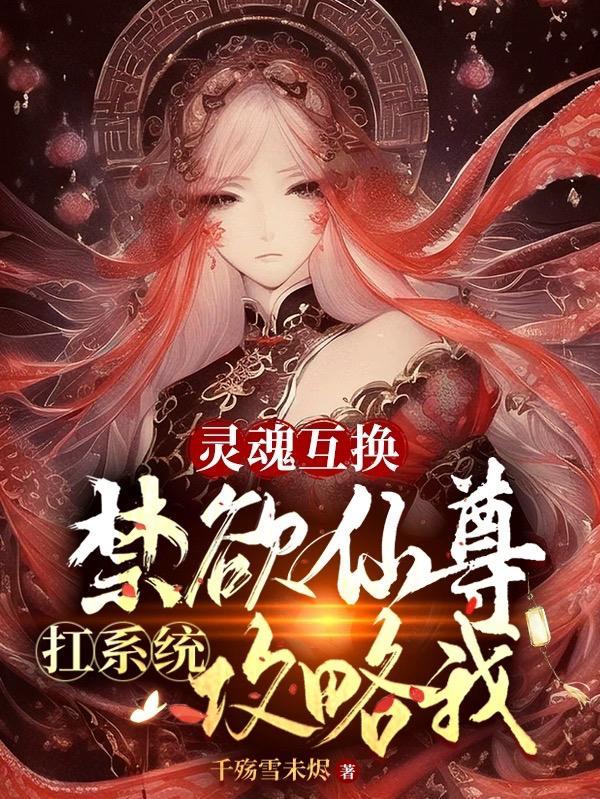乡村文学>这次我成主角了 > 第31章(第1页)
第31章(第1页)
宗政祁眼皮稍稍掀起一点,看着程思源的眼睛,又问:“这里可以吗?”
程思源缓缓垂下眼睫。
宗政祁却没有继续,依然不依不饶地盯着他,声音很轻:“如果我问你的话,就回答‘可以’或者‘不可以’。”
然后他又耐着性子问了一遍。
程思源咬了下后牙,深吸一口气,回答:“……可以。”
宗政祁这才勾起一个笑容:“乖。”
那只手丈量出的领地还在扩大。
每当程思源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反应时,宗政祁都会停下来,不厌其烦地问他,这样可不可以,并且要求他给出明确的回答。
其实程思源已经觉得有点不可以了。
但或许是宗政祁的语气带着某种引导的意味,也或许是程思源回答“可以”之后,对方夸奖的语气十分温柔,于是在宗政祁的手已经靠近一个危险的地方时,他还是鬼使神差地说了句“可以”。
宗政祁动作一顿,然后直起身。
225
“自己去喝口水,然后躺到床上去。”
程思源“哦”了一声,先站了起来,然后弯腰想把睡袍重新捡起来,衣角却被宗政祁踩住。
他抬眼和宗政祁对峙片刻,接着妥协地松手,起身去茶几那里喝水。
他背对着宗政祁,听到他拉开了抽屉。
“?”
程思源放下水杯,挪了过去,老实躺好。
接着他看到宗政祁拆开的其实是一只手套。
男人垂着眼皮,神色显得有些倦懒,慢条斯理地将黑色的薄手套戴在右手,让它和手指贴合。
手套拉到掌根处,活动时会露出半截冷白的手腕,和自手套里延伸而出的青筋。
吊灯直接照在程思源头顶,他突然沉默了一下,低头看向自己的肚子。
说实话,现在这个场景,让他有种自己躺在手术台上的错觉。
如果对方不是宗政祁的话,程思源可能差点要报警说有人要打他肾和腰子的主意了。
一只手给他挡了一下直射眼睛的灯光。宗政祁调暗了吊灯,低沉的声音里带着点笑意:“在想什么?”
这是一个问句,于是程思源如实回答:“感觉要被割腰子……”
宗政祁一愣,随后扬起眉毛:“你更喜欢那种玩法?”
程思源立刻摇头:“不不不不……”
宗政祁便低沉地笑出了声。
他在床头坐下,那声音几乎就在程思源的耳边。
嗓音如同带着一点磨砂质感的低音提琴,从鼓膜传递到大脑时,程思源感觉自己头皮的每一寸细小的皮肤都战栗了起来。
宗政祁又说了些什么,那只没有戴手套的大手轻轻搭在程思源头上,手指穿过柔软的头发,安抚地摩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