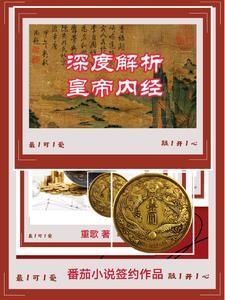乡村文学>综穿之时空历练记 > 长安诺187(第1页)
长安诺187(第1页)
到了新婚夫妇结饮合卺酒的时辰了。
她刚走出门,念岑就送奉岑到了婚房门前。
两人把门从外面合上,相视一笑。
“念哥哥,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亲生母亲的事?”映淳心疼地望着严念岑的面庞,想从他脸上看到阿今当年的模样。
念哥哥这样好看,阿今一定生得很美。
“嫂嫂给你讲的?”念岑温润的一笑:“小的时候,大哥总因为母亲的事生我的气。”
“他怨我与母亲那样相像,却不记得她的样子,也没有亲口叫过她一声娘。”
“我想,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严念岑笑的时候,一双美目也是弯弯的:“一生中遇见过那么美好的人却又失去,该是怎样的蚀骨之痛。”
映淳忽然想起温月延最后给她讲起的,兄弟二人名字的典故,忽然一下子扑进念岑怀里把他搂得紧紧的。
奉岑,念岑。
我将永远崇奉思念着你,我识于此山葬于此山的爱人,我最亲最爱的阿今。
映淳从内院里走出来,见满座宾客已陆续离席,严海和念岑正在门前送客。
我正和严夫人闲谈着,映淳转了一大圈没找到父亲,凑到我身边疑惑道:“娘亲,爹爹去哪儿了?”
“郑王差人来请他到府上小酌一杯,他才坐了郑王府的马车走了。”我浑然未觉有什么问题:“让咱们一会儿先回王府,不必等他了。”
“二皇伯一把年纪了酒瘾居然这么大,这个时辰还叫爹爹去喝酒。”映淳却敏捷地察觉到了些许异样:“爹爹才得胜凯旋,他就一刻也等不得,急得要从别人家的婚宴上把爹爹请走——”
“淳儿,你的意思是?”我紧张地站了起来。
“弟弟之前跟我说,要我当心二皇伯,”映淳忽然想起启焕之前跟她说过的话:“他虽然看似行事不偏不倚,说到底还是个保皇党。”
“我先找师父和十皇叔想想对策,以防二皇伯做出什么对爹爹不利的事儿来。”映淳向严夫人一点头:“师娘,劳烦您陪着我母妃聊聊天,我们很快就回来。”说罢就扭头跑出了门。
“映淳郡主这行事果决的飒爽劲儿,一般的男子都比不上的。”目送着映淳出了门,严夫人不禁由衷向我称赞道。
“我家小姐当年,也是这样,一旦遇到了什么事,立刻就能拿出主意和决断来。”严夫人眼中忽然充满了怀念之情。
我知道她说的是那位已故多年的先夫人,一时也跟着有些黯然。
萧承煦才踏进郑王府,就意识到自己赴的是场鸿门宴。
前厅置了许多张长桌,朝上的亲贵大臣与宗氏族亲都立于厅中等待,见他来了,众人纷纷鞠躬合手行礼,并向两侧避去,为他让开一条路。
“九弟,你来了。”郑王年迈,这两年添了个咳喘的毛病,说话时还忍不住轻咳两声,声音很是沙哑虚弱。
“二哥。”萧承煦向郑王行了一礼,冷笑道:“真是让人意外啊,说好的小酌,怎么成了大宴?”
郑王面有赦色,尴尬地环视一周,解释道:“都是自家人,大家没事就都聚在一起,当然像大宴那样热闹了。”
这番牵强的说辞,听得萧承煦的眉头都皱了起来。
“你们大家先出去,我和摄政王有几句话要说。”萧承礼抬袖示意众人离开。
偌大的前厅中,顷刻间只剩下兄弟二人。
“二哥有话便直说,尽管交代弟弟便是。”萧承煦强压着怒气先开了口。
“好,都是自家兄弟,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萧承礼似乎就等着他这句话:“如今皇上已然大婚,你为何不肯交出玉玺章印?”
萧承礼用谴责的目光盯住萧承煦的面庞:“是不是,不想放权还政啊?”
“我身负摄政之责,陛下一日未亲政,我理应,掌管玉玺和章印一日,待陛下有能力独当一面,可以亲政之时,我自会选个良好时机,将玉玺章印双手奉上。”萧承煦语气坦荡,字字铿锵。
“可我却听闻,是你摄政王自己想要当皇上。”
“没有的事。”萧承煦藏在广袖中的拳默默攥紧。
又是这样,难不成,他们这次又要寻什么花样让他认下莫须有的罪名吗?
“当真?”萧承礼眸中颜色晦暗,抬眼紧盯住萧承煦。
“二哥一直看着呢,我怎么敢。”
“你现在自然是不敢。”萧承礼的情绪忽然激动起来:“可是你把住手里的权力不放,等到皇上忍耐不住的时候,你就找出借口,说自己是被逼无奈才谋权篡位的,是不是?!”
这一阵情绪来的凶猛,老人一下子开始剧烈咳嗽起来。
萧承煦忙快步走过去,帮萧承礼抚着脊背顺气。
“可怜,我那两个儿子战死在沙场上。”萧承礼忽然悲痛地泪湿眼眶:“可是…可是却是为了一个乱臣贼子而白白送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