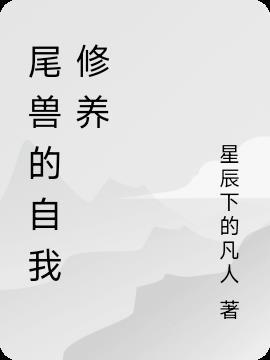乡村文学>沼泽里的百合花 > 第98章 约翰米娅心灵的默契沟通(第1页)
第98章 约翰米娅心灵的默契沟通(第1页)
米娅把长头剪了。以前为了省钱,我们从来不去美容店,约翰的头都是她剪的。她的头像草一样越长越长,要么一把扎起来,要么盘在头上,从来不打理。现在,头被剪得齐耳短,在她细长的脖子上方甩来甩去。前额的刘海如刀切一般,盖住了眉毛。本来并不很大的脸盘好像缩小了一半。看来米娅是故意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娃娃脸。她穿一件紧身的白针织毛衣,外面是有背带的工装牛仔裤,我一眼就认出这条裤子是新买的,因为她从来不穿西式短裤,连裙子都很少穿。看她露着两条白白的大腿,我心里不是滋味。
她笑嘻嘻地站在我的面前,好像在等待我评论她的打扮。说实话,我不喜欢,一点也不喜欢。唉,也许说不喜欢有点过分,那么至少是不习惯。我们结婚八年,米娅已经3o出头,干嘛搞得像个孩子一样?尤其在这春寒料峭的晚上,露着两条大腿,不怕着凉吗?
但是,约翰还是笑了一下,说道把短裤换了,当心感冒。
没关系。她一边跟在我后面进了客厅,一边说,下面穿着长袜裤,不冷的。
这时,约翰有点火了,一股无名之火涌上心头。我狠狠地把领带扯了下来,头也不回地进睡房,把西装脱了,套上了一件旧毛衣。
米娅一直跟在我的后面,她帮我把西装挂上衣架,跟我回到客厅。约翰打开了电视,看当天的新闻,米娅坐在我的旁边。我什么都看不进去,干脆关了电视,对她说,我把书借回来了,在皮包里,晚上你抽空看看吧!
她说,约翰,我很有信心,我有大学学位,有夏华推荐,面谈会成功的。
我说,还是准备一下好,今晚早点睡,明天几点去?
1o点。美国人喜欢睡懒觉。她笑着说。
那天晚上,为了让她读书,我从冰箱里取出一个降价时买的比萨,胡乱烤熟,两人草草吃了,然后独自插上碟片,看了一个中国的老电影。米娅在睡房里看她的幼儿教育书。
电影里有男女相爱的镜头,但是拍得很含蓄,点到为止,没有美国电影里赤身裸体的床上大戏。我觉得艺术应该是这样的,爱情的美应该在眼睛里,由眼睛来传达心灵的感情。而不一是在大腿之间。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约翰也曾经图新鲜,去看那种刺激电影。没有看完就出来了,简直恶心极了。人们说
大陆因为性压抑,许多人出了国看刺激电影解渴。我很难理解,没有爱情的泄和动物有什么两样?尤其是女人,要性要得像孩子要吃奶一样,真是白活了那把年纪。
我想起自己和米娅之间,总是缓缓地幽雅地进入情绪,从来没有急不可待,好像原子弹爆炸没有明天那样的末日情怀。刚结婚的时候,因为米娅个子小,我甚至找不到应该去的地方,只好被夹在两腿之间,照样心满意足。
看完电影,我有点激动,也许是白天有了那份好心情,也许是对过去性生活的回忆,我感到体内有了张力。
米娅,你先洗澡吧!今天早点睡。这是我们之间的暗号,因为平时洗澡都在早上。米娅答应着,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说来奇怪,以前我对这种声音从来不加注意。这时,却觉得特别好听。水管轰鸣,水声流畅,好像一支小提琴协奏曲。我不禁想入非非,想到了以前和米娅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在月光下散步,想到了看电影的时候,悄悄地捏着她的小手,想到了第一次接吻心跳如鼓······
洗完了,约翰你来洗吧。
米娅叫我的时候,我还陶醉在想象中,仿佛如梦初醒,赶快从沙上起身,进了浴室,三下两下把衣服脱了。这时候,我现自己的状态特别好。我故意把水开得烫一些,心里想,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今晚应该很开心。
更令我高兴的是,走进卧室,看到床头柜上点了两支蜡烛(那是我们为防断电而准备的)。茫茫夜色中豆火点点,令人心神摇曳。米娅已经躺在被窝里。收音机开着,轻松的乐曲,音量很低,伴着肥皂的清香味,在空中缭绕。我笑了,心里甜滋滋的,把裹在上身的毛巾解开,便上了床。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如此美好的心情和欲望,在掀开床单
以后竟然被破坏殆尽。米娅,这个温柔顺从的女人,从来都是由我来安排的老婆,此刻却一丝不挂地躺在我的旁边!我都穿着短裤呢!她把自己剥得精光!
说句心里话,结婚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裸体的老婆。我们的衣服都是上床以后脱的。我对她身体的了解从来不通过视觉,而是用手摸出来的。每次做完爱,我们都把衣服穿起来再睡,生怕着凉感冒。现在,迷迷蒙蒙的烛光中,我看到一个女人的肉体,和画报里的淫女没有什么两样。我像个木头人那样坐在床沿上,呆呆地望着燃烧的蜡烛。透明的烛泪在微光中一点一点滑落下来,好像在为我而哭。
她怎么啦?为什么在双方还没有进入情绪的时候,突然想把乳房和阴部暴露在外?唉,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就是在外面多了一层包装?所谓文明,不就是因为有羞耻之心?
我用毯子把米娅遮住,给自己穿上衣服,跑到客厅去了。
开了电视怕闹,关了又觉得窒息。我随手拿起一本杂志,封面上一对男女正在亲嘴。这种杂志到处都是,我从来不以为然。可是,这时却像侮辱了我的眼睛似的,不禁义愤填膺,破口骂人。不要脸!用私情卖钱,不仅肮脏而且虚假,谁相信这种玩意儿?我想起了白天米娅的英文电话,想起了傍晚她穿的那身衣裳,想到她在床上的表现,心里一团乱麻。一个贤惠端庄乐于付出的女人,和美国人沾了点边居然变成这样!
见鬼去吧!约翰把杂志卷成一团扔向天花板,希望它头破血流,粉身碎骨。我意识到那张带有广告的报纸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想来
就是在这时,我现米娅正坐在沙的那一头,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跟过来,也不知道她坐了多久?我躺下来,故意背朝外不理她。她也不说话。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
想去,觉得明天的面谈没有必要再去。一来,这个面谈并不解决绿卡的问题。二是如果佩芬进了美国人家,住上二三年,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用老婆去换绿卡,很可能两败俱伤,这条路千万走不得!我还是应该在研究上加把劲,只要成果重大就可能被学校留下来。解决家庭生计本来就是男人的事情,我还不见得那么没有出息。
想到这里,约翰撑坐起来,对米娅说,去睡吧!明天的面谈不要去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答道,我累了,明天再说吧!
说完,我关了灯,躺下便睡。我的鼻子贴着沙罩上的粗纤维,呼吸不畅。这个沙很旧了,是别人丢弃的。鼻孔有点痒,想打喷嚏,却打不出来。我想换个睡姿,却因为弹簧松软,费很大的劲也难以挪动身体。只得扭一下脖子,让鼻子和纤维保持距离,睡得很不舒服。迷迷糊糊中,我看见墙上挂了一个巨大的电视屏幕,一会儿亮,一会儿黑,看得我头晕目眩。我的手不停地在电脑键盘上敲打,就像弹钢琴一样,把大量的数据输进去,输进去。屏幕开始出现变化,由灰变蓝,由蓝变绿,由绿转红,花瓣一片又一片,落满屏幕。霎时,光芒万丈,同事们围绕在我的周围,鼓掌喝彩。屏幕上的鲜花变成了佩芬的脸,抿着小嘴朝我微笑。米娅!米娅!
约翰哥,你怎么啦?
我睁开眼睛,现台灯亮了,米娅跪在我的面前。
没什么,做了一个好梦。我打了个哈欠,笑着说。
回房去吧!睡这儿要着凉的。
你怎么不去睡?
米娅不语。我知道,如果我不走,她会陪着坐上一夜的。
唉,这就是我的老婆,那个委曲求全的弱女子米娅。
我一开心,便从沙上起身,一把抱住她,一直抱到卧室的床上。米娅个子小,每每抱起她,我有男人的自豪感。她哭了,身体在我的怀里不停地抽动。我搂住她说,米娅啊,别哭了。你知道吗?我不舍得你去吃苦。别再想绿卡了,我们好好睡一觉。
我像以往那样,让她睡在我的胸口,一边抚摸她的皮肤,一边把她的汗衫从肩膀上往下卸,再缓缓地把她的短裤退下去,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在她身上摩擦。米娅任我摆布,就像一只乖乖的小绵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