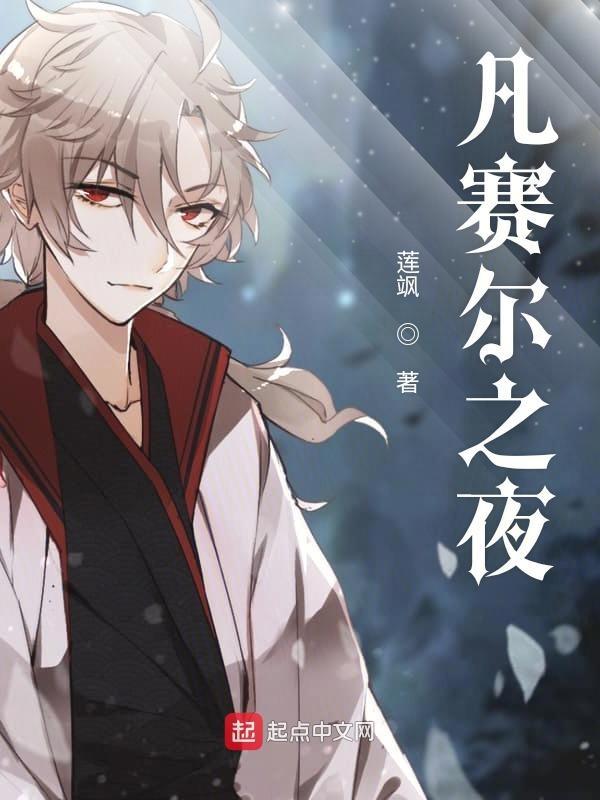乡村文学>前任结婚告诉你的心理 > 第97章(第1页)
第97章(第1页)
“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问他在哪儿。”饶时说完就挂断电话,过了半小时,他又给高一顺打了过去。
高一顺语气听着不怎么样,他说:“你俩在玩我啊?”
“什么意思。”饶时问。
高一顺说:“于桑洲说他和你在一起。”
饶时看了眼只有他自己的出租屋,对电话那头的高一顺“嗯”了声,挂断的那一瞬,饶时想往死里揍于桑洲。
脑子里有无数个“为什么”想问,就连电风扇的声音都惹得饶时心里不痛快。
他也是不死心,自己又给于桑洲发了条消息,他问:今天要给你留门吗?
于桑洲应该不忙,他都辞职了,还能有什么忙的。
果然,于桑洲没过两分钟就回了过来,他说:不用留,你早点休息。
饶时回复:那晚安。
于桑洲:晚安。
安不了一点。
饶时恨不得逛遍江城每个角落,把于桑洲揪出来,先给他两拳,后给他两脚,最后再问他,你为什么不回来。
可他找不到于桑洲。
于桑洲身上也没有定位标记。
要是他之前在于桑洲身上装过监控就好了。
隐形小巧,能够埋进皮肤,走进血管,融入血液里的监控。
那样于桑洲就能一直活在他眼皮子底下,那样他就能不再这样患得患失。
饶时没提起自己已经知道他辞职的事,相处也和以前无异,高一顺肯定也没说。
因为于桑洲的理由依旧是加班。
饶时只当不知道,他想看看于桑洲到底想骗自己到什么时候。
这段关系对他来说就是一把钥匙。
一把代表“家”的钥匙。
饶时不能替于桑洲决定到底要不要回家,但这个“家”,饶时不想让它崩塌。
任游在几天后来了一趟千湖区,饶时问他过来干什么,任游拿出手机就开始扒拉聊天记录。
“你看看你每天丧气得跟什么一样,”任游扒拉几下都有些看不下去了,他将手机熄了屏揣进裤子口袋里,“晚上带你去喝点儿,把你这萎缩的小脑好好治一治。”
饶时不太想去,但抵不住任游一劝再劝连拖带拽地给他带出了门。
“去哪儿喝,”刚出门就热,饶时擦了擦额头的汗,“我吃不下去,不太想吃。”
“纯喝,”任游说,“有家新开的酒吧,你正好换个环境待待,让你的神经受点刺激,整天这么萎靡不振的,我真是看不下去。”
酒吧不远,坐出租车过去十分钟,进去还没一分钟,饶时就想掉头走。
“坐下,”任游一把给他按下去,朝他耳边大声说话,“玩会儿再走,别的事改天再想!”
“我什么都没想!”饶时感觉地面都在震动,音乐声吵得他耳朵疼,他拽过任游也大声道,“最多俩小时,不然我要聋了!”
任游点点头,叹着气拍了拍饶时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