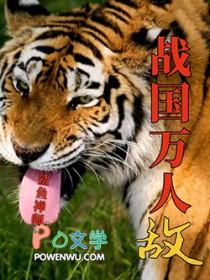乡村文学>火影剧情 > 第17章(第1页)
第17章(第1页)
“明明是你忍不住。”他粗鲁地恶语,对于鲜血淋漓的身体的尖叫置若罔闻。
“是吗?”我居高临下地冷笑,“从头到尾都只是个无聊的误会。”
“真是个嘴硬的家伙。”他孩子般伸手触摸了我的腹肌,柔软的指肚向下延伸,轻而易举地攥住了我的私密,“还是误会吗?”
“不要再插手我的生活了,”我打掉了他的手,“我的一切都要被你毁了。”
“我没有插手,我只是看着。”他舔掉了唇脚的血线,“你的生活本来就是碎的,我只是让你看清了而已。”
“会有人把你轰走的。”我警告完,故意露出得意和胜券在握的表情,然后扬长而去。
【漩涡鸣人】
我一定是撒旦的宠儿。
佐助是耶稣放置于这世间的金尊玉器,光洁无暇、炫目勾人。一份正当的工作,一张漂亮的面孔,一段完美的婚姻,一个无懈可击的身份。因此,当我一点点撕开他的时候,总是感到情难自抑。
“别回家了。”我咬着他的耳朵私语,“正常人的日子?说什么鬼话。”
“呵呵,难道你就在过好日子?”他冷嘲热讽、鞭辟入里。
我当然算不得幸福,一周之后我找到的新工作是坐台陪酒的歌手,只需要随意撩拨吉他,然后出卖色相。我无意哼出第一次见到佐助时昏昏然听到的摇滚。
“嘿亲爱的,遇到你的时候刚刚好。我喜欢你、这点不用多说。亲爱的、你的气息真是迷人,请让我拥你入怀一辈子……”
美酒欢歌,我唱得动情,全然不顾四面八方的嗤笑。直到粉红色的灯雾忽然把我贯穿,五颜六色的光斑涤荡在我的身上。我撂下话筒径直走向后台,叼着烟头的毛头小伙嘲弄地点戳我的胸膛:“唱的真烂啊,词都错了。”
“妈的老子醉了,老子就要唱!”我推开他坐到架子鼓前,疯狂地敲击着踩镲和底鼓仿佛敲击着我的脊梁。
威士忌被疯狂摇晃,拔出瓶塞滋了我满头满身,湿透的感觉让我回到了满身烂菜根的童年。我听着他们的起哄和倒喝,虚无的欢愉神似地狱的魑魅魍魉。无情的拳脚聚焦到我的身上,残忍的疼痛让我痉挛发狂。我是一块肉,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我的魂被佐助偷走了,离了他我什么也不是。
后半夜我偷空在后门吐得七荤八素,眯眼仰望星空的时候看到那个混蛋遮住了月亮。
“白痴,”他双手抱胸居高临下,掐掉了左手里猩红烫眼的烟头,“你唱的,算情歌吗?”
“怎么?”我抹掉了嘴角的血迹,像个滥情的混蛋伸舌甩头,“爽到了?”
“这里不是gay吧。”佐助漠然地看着我,“下次换个地方发疯,没人喜欢自作自受的苦情戏。”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我靠着满是低俗恶语的墙面,“好好先生不该陪老婆吗?别告诉我上司会让一个敲代码的玩潜规则。”
“睡不着罢了。”他冷哼了一声,“这里有的是陪酒的。”
“有纸笔吗?”我像块软泥松弛地瘫倒在墙角,佐助从上衣口袋里抽出带盖的圆珠笔,顺带附上了自己的明信片:“没纸,凑合写这儿得了。”
“穷酸。”我翻了个白眼在他的大名底下龙飞凤舞地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活好的话打八折。”
“哦豁,你还在乎这个?”他讥讽地挑衅我的下颚,修长的手指钻入我的口腔,抵住了唇舌,“我以为你来者不拒。”
我闭着眼睛专心地体味这偷情般的暧昧:“我不宰回头客。”
宇智波佐助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我他妈早就心知肚明。我和我的初恋爱得像对定时联络的地下党,xx的时候还要担心被吊销驾照。买xx的时候要挑选最大码照顾他该死的自尊心,xxxx要扭曲身体躲在死角防止被拍到。
似乎我们就会这样过下去,把每一周的恶意宣泄在名为“加班”的深夜里。
“我要走了。”我打开车灯开始收集xx和xxx,“怎么样,有什么话想说?”
“去哪里?”他拍了拍上衣的,重新开始打领带。
“纽约。”我快乐地吹呼哨,“州政府打电话让我回去,或许是要把我再送进监狱。”假话,州政府说我的dna和一个叫波风水门的富豪匹配上了。
“你坐牢上瘾了?”佐助皱了皱眉,“还是我钱给少了?”
“哈哈哈哈,”我放声大笑,“别担心,要是被冤枉我撒腿就跑。”
“哦。”他低头开始整衣领,然后把xx收进了电脑包。
“你呢?”我的脚趾穿过他尚未扣好的衣尾,肉麻地贴在他紧绷的小腹上,“什么时候离婚?”
“看情况。”佐助耸了耸肩,“你知道,财产分割是一笔大开销。”
“假如,我是说假如,”我揉着下巴颔首看他,“我足够有钱,你愿不愿意?”
“做你的青天白日梦吧。”他嘲讽地把颈枕扔给我,“有钱了你找谁不好?”
“说的也是,”我摇了摇头,“但我会分你一半。”
他异样地抬眉看我,像喝了假酒一般促狭轻笑:“白痴。”
“我是认真的,”我伸了个懒腰,“你救了我的半身,我总该支付一些报酬。”
“我不是你。”他冷哼了一声,“我什么都不缺,也什么都不要。”
【宇智波佐助】
人总是贪婪的。
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很少用真金白银来衡量感情。鸣人是个例外,对着他我总是在想既要又要还要。我知道这是场荒唐而不知足的索取游戏,可偷来的欢愉总是像糜烂的罂粟,勾人而痴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