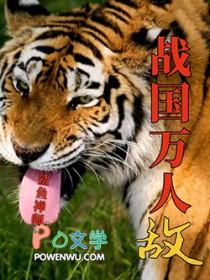乡村文学>表姑娘她总表里不一免费阅读 > 第57章(第1页)
第57章(第1页)
“好好好,礼成礼成,我说妹夫,咱们是不是该定下这大喜的日子了?也好腾出手来操办,这一回定要亲事热闹些才好!”
侯夫人裴氏性子急,这礼既然已经过定,那便行正事要紧。
她开口倒是省了裴夫人的话,于是裴夫人让身后的嬷嬷又送上一份烫金帖子的册子,而后言道。
“两个孩子的生辰八字我已找人算过,今年的十月初八,亦或者明年的三月二十皆是上上大吉的日子,不知姜宗正意下如何?”
按着姜怀山的性子,自然是越晚越好。
可他也深知这未来女婿的脾气,便是自己选了明年的那一日,只怕最后还是要落在十月,还不如一开始就敲定的好,于是摸了摸颏下的胡须后,略做思考后就定下了那十月初八。
他一开口,其他人都觉得日子可能有些仓促,唯独裴子谡满意的看着未来的岳丈大人,开口就说道。
“姜伯父放心,我一定将此事办得风风光光。”
“好,好,子谡有心了。”
订亲的整件事,大多数都是裴家人和姜怀山并文渊侯府来说,热络且开心的就商量着那些细节处,姜老夫人插嘴过两句,却都没什么人在乎,所以到最后她也就只能闭了嘴。
眼神一点不错过的看着众人,她都是想说点什么,奈何无人肯听,直至此事结束,送走了裴家和文渊侯府的人以后,她才在泰安院中大发雷霆。
恨不能将手边的东西全给砸了,才能消解心头之怒!
姜时槿心中也是不爽的厉害,可这种时候她要是自己去出头那就显得有些蠢了,因此故作不知的上前去就安慰着姜老夫人说道。
“祖母这是怎么了?大喜的日子,大姐姐的亲事落定,不是该高兴吗?”
“落定?高兴?你刚刚没瞧见文渊侯府的那些人有多蹬鼻子上脸吗?说起来也是笑话一场,明明是我姜家姑娘要嫁人,怎么好似全被他文渊侯府把风头抢去了,尤其是那老夫人和侯夫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竟让我这个正经的祖母插不上话,到底还有没有将我放在眼里了!”
姜老夫人骂骂咧咧的,恨不能再砸几个碗碟消消气,可看着那一地的碎瓷片,忽而又觉得心疼的很,于是捶胸顿足的厉害。
见此,那姜时槿不着痕迹的说道。
“许是大姐姐更亲昵侯府的亲人罢了,毕竟是在那边长大的,这个也怪不得大姐姐,倒是大伯父怎么也偏帮的厉害,我瞧着他似乎对于裴家人有些怵呢。”
“谁说不是啊,咱们槿儿嫁的是淳王世子,是正经的皇亲国戚,也未曾见大伯如此表现,怎么反而对着一个为臣的裴家这般姿态,要是被人给传出去说我们姜家惧了裴家的权威,反倒是让人说嘴了呢,婆母。”
二婶张氏看热闹不嫌事大,不管好坏总是要塞几句难听话到姜老夫人耳中,她起先怪罪的大多是文渊侯府,可现在怨恨着怨恨着连自家儿子也有些瞧不上了。
于是抹抹眼泪,就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痛骂了两句。
“没根骨的东西,从前就怕他岳丈家,如今连女婿家也怕上了,我瞧啊,以后人人都能踩在他头上,顺便把我们姜家的脸面也丢地上践踏就是!我怎么会生出这么个没出息的货色来!还不如老二呢,他若是还活着,你们母女,咱们姜家也不至于受这份欺负了!”
祖孙仨方识真面目
姜老夫人的一番话,让一贯张牙舞爪的二婶张氏突然沉默了下来。
仿佛数十年的委屈都在这一时半刻间要倾泻出来似的,只见她眼泪跟珠子似的就掉下来,比之刚刚在姜时愿订亲仪式上的硬挤出来的那两滴要真心的多。
而姜时槿对于父亲的印象薄弱得太多太多,相比较之下,她儿时大部分的记忆都落在了大伯父身上,只可惜彼时她视作天的伯父此刻眼中只有他的亲生女儿,因此这姜时槿也是一边佯装落着泪,一边就算计起家门来。
祖孙三人好一顿哭,到最后还是姜老夫人先一步收住了泪。
她丧父丧夫丧子皆经历过,倘若没点硬本事,也撑不到现在。
所以比起娇滴滴的躲着落泪,她更喜欢能找补回来,比方说她此刻就想在那泼天富贵的聘礼上动手脚,好让那父女俩也知道知道,这姜家门里头她这个老婆子还是能做得了主的。
“行了,别哭了,我们就是哭瞎了眼,老二也回不来,还不如想想眼下怎么把日子过好呢,看今日裴家这派头可不是昨天侯夫人上门来随便言语的那种,那裴子谡到底是什么人物?槿儿,你可有打听过?”
姜老夫人身边无人,平日里连西京城中的席面也不大会有人邀请,从前看在文渊侯府的面子上,倒是去过几次,但可惜自从两家因为退亲一事翻脸后,就再无帖子相邀了。
因此她打听事情,无非就是从下人们嘴里听些传言罢了,所以她对于裴子谡这位汉州裴家小将军的情况,了解甚少。
张氏亦如此,还觉得裴家人没有淳王府身份尊贵体面呢。
而被问话的姜时槿,如同哑巴吃黄连,但前有世子的施压,后有赵家姐妹即将入府的逼迫,她想借助家中之力,那就不能不直言相告,于是蹙眉说道。
“孙女此前也是不大了解的,昨日大伯父让人送了帖子去淳王府后,我才听世子提起过,裴家在西京城不怎么有名望,但是在汉州据说是说一不二的大家世族,又因为出了好几代的将军,所以兵权贵重,据说掌军四十万,其中绝大部分的就握在这位裴小将军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