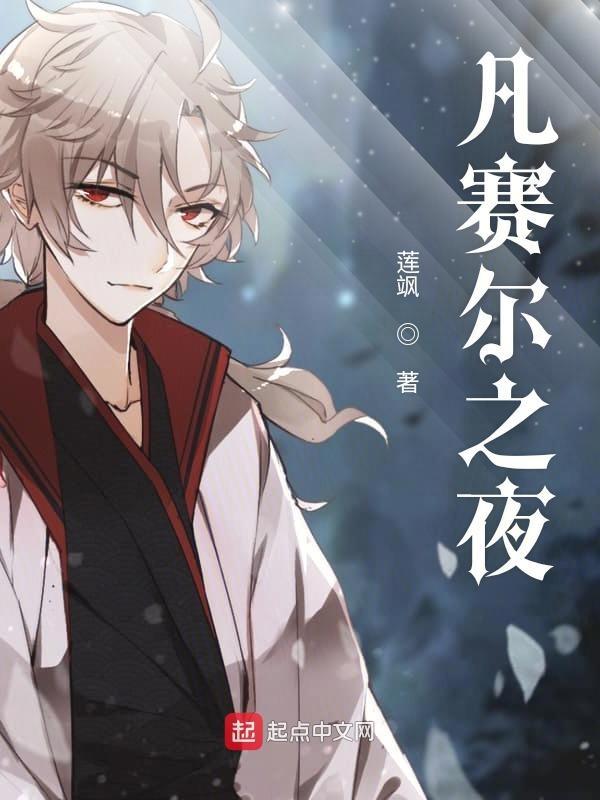乡村文学>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来到了 > 第131章(第1页)
第131章(第1页)
钱平桥傲然负手:“你要得太急,这火炮徒有其表而已,无法填火。”
良辅狡黠一笑:“无妨,不过吓吓他而已。”
冰心玉壶
第二日,良辅代景福临为使臣送行,送至定安门时,金光谦逊有礼:“不劳先生远送。先生学识渊博,令人称奇,在下钦佩不已,若有机缘,可否结交一二?”
良辅彬彬有礼:“哪里哪里,在下才疏学浅,只是平日里最不喜人不学无术、胸无点墨,才不要和不读书的人做朋友呢。”
金光:“……”无法反驳呢。
良辅使命达成,准备回宫。迎面看见定安门墙角远远站着一个人,两眼红得跟兔子似的,眼看着泪花就要“吧嗒”往下掉。
良辅自己回想了一番自己说的话,“平日里最不喜人不学无术、胸无点墨,才不要和不读书的人做朋友”……
于是,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杨天虎,听到了这番话,然后红着眼睛转身就跑。
良辅心里一急:“元霸!把人给我拦住!”元霸被良辅喊得脑袋一炸,自家大哥真的是从没有这么着急过呢……
元霸应声就去追,但是!这里可是定安门啊,投壶、蹬竿、吞剑、走火、顶碗、耍盘,乱成一锅粥的定安门啊!
元霸这一路上撞得鸡飞狗跳鸡犬不宁,好容易在永安街巷子口把人给堵住了,良辅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后面跟。
良辅追上来,手撑着墙,把人堵着,气还没喘匀:“你……你跑什么啊……真跑死我了……”杨天虎哭得梨花带雨可怜巴巴,抹了抹眼泪,闷声说了句:“跟我来。”
良辅脚都跑废了,认命在后面跟。到了巷子里一处民宅,杨天虎推开门来,院子里一箱一箱全是行李,他不说话,默默地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打开给良辅看,一边开一边说。
“这一箱是裘衣裘毯,北边冷,你受不住。这一箱是果干肉干,北边那么远,路上饿了可以吃。这一箱是药,肚子痛的,头痛的,发热的,风寒的,每种都有,当然我是不希望你生病的但是万一你哪里不舒服人多手杂总有顾不到的好歹还有药防身……”
杨天虎一边抽搭一边细声细气地说,良辅靠在院子门口喘着气,自从北境的消息传回来,这三个月里自己都在干什么呢?
先是盘算了一遍朝中目前的局势,哪一家可用,哪一家要反,哪一家可以争取,再细算了一遍军中兵力分布,此次赴北哪一边要去,哪一边想去却绝不能容许去,哪一边不想去却要想方设法逼他们去,再然后,还要算一算银子……
景福临想得到的,良辅都要想到,景福临想不到的,良辅也全帮他想到了,连傅达礼都狠下心送出去了,能用上的一个也不能放过,更何况他自己?
他只是想不到,算来算去,还有一个杨天虎,背着这么一箱一箱的东西,从万里之遥的湖广,一步一步走到了京城,走到了定安门,走到了自己面前。
良辅跑得急了,一口气上不来,一颗心突突跳着,跳得他心烦意乱。
数完了这一院子的行囊,杨天虎又细细地一个个把箱子封好,低着头,巴巴地说了句:“你,你保重,我,我走了……”一句话未说完,眼泪又吧嗒吧嗒掉下来了。
索性不再说些什么,埋头往外走,良辅堵在门口不动,杨天虎带着哭腔,磕磕巴巴地说:“请,请你,让一让……”良辅不让。
杨天虎也不敢抬头,就侧着身子准备穿过去,良辅突然倒下去,横在杨天虎面前,杨天虎大惊失色,慌里慌张伸手去扶,将人险险扶住,良辅就势扑在人身上,抱紧了不松手。
杨天虎又是惊又是羞:“你,你,放手!”
良辅把头埋在他脖子里,双手圈住他不放,嘟囔着:“痛……”杨天虎吓得不行:“痛?哪里痛?为什么痛?看过大夫没有?你身上怎么这么烫?是不是在发烧?我去给你找大夫!”
良辅被他吵得心烦,摁住他脑袋在他唇上“吧嗒”亲了一口:“再说就亲你。”然后仍又将脑袋蜷在他颈窝里,把人压在门板上圈着,柔声说着:“别动,让我抱抱。”
杨天虎一张脸烧得要冒烟,手足无措,也不敢动,由着他抱着。过了许久才敢将手搁在他背上,轻轻地回手将良辅抱住,眼泪又控制不住淌下来。
“啧。”良辅咂了咂舌,狠亲了杨天虎一口:“再哭就亲你。”不说还好,一说杨天虎哭得更凶了,良辅眯了眯眼:“这可是你自找的。”捧着杨天虎的脸,倾身吻下去,缠绵厮磨……
元霸坐在箱子上,全程懵逼,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尉迟将军府,尉迟秋云一身银甲,三千精锐整装待发。锦衣玉食的小公子,戎装加身,平添三分英气。
“我和你们一样,有心上挂念的人,正因如此,只能以你我血肉之躯为盾,让心上挂念之人免风尘侵扰,此战,只能胜,不能败。明白吗!”
“明白!”
尉迟秋云点点头,巡视着三千将士,视线扫过某个角落的时候,忽然顿了一下,尉迟秋云铁青了脸色,怒喝一声:“出来!”
没有人动。
其余将士眼观鼻鼻观心,没有一个交头接耳或是左顾右盼。
尉迟秋云冷笑了一声:“怎么,还要我亲自动手么,燕三小姐?”
整个将军府死一样的静。燕云渺气呼呼地从阵列里走出来,解开头盔,扔到尉迟秋云脚下:“凶什么凶!你当没看见不行么!”
尉迟秋云不看他,冷声喝令:“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