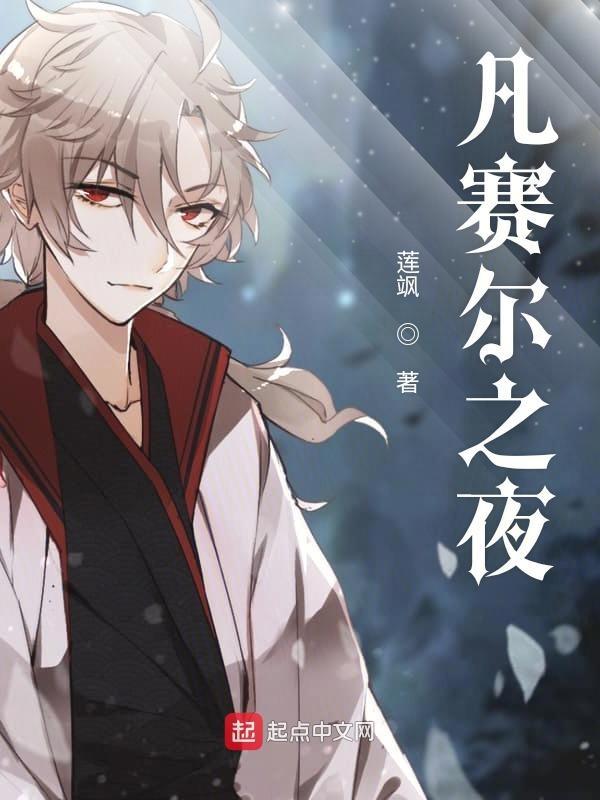乡村文学>低声细语百科 > 第50章(第2页)
第50章(第2页)
傅冬川突然接了话。
“你会被诓住。”
“什么?”
“像致幻剂。活在这个城市的感觉并不真实。”傅冬川目视前方,对他毫无保留:“我陪老总们出去吃饭,每顿几千几万很正常。”
“蓝鳍金枪鱼,怀石料理,鹅肝慕斯,马粪海胆……”
“长期和那些人相处,再看见捡纸壳饮料瓶的残疾老人时,我感觉自己同时站在好几个幻觉里。”
至高处的奢侈精致,低落处的平凡窘迫,以及毫无链接感的当下。
周筑用指腹剐蹭着纸盒的边沿,许久开口。
“所以我们每天从幻觉a起床,去幻觉b上班,穿过幻觉c下班,然后结束这一天,无限循环。”
“可是你很真。”傅冬川不假思索道:“我在看到你的第一眼,就很想把你留下来。”
“你那天连简历都没带,在倚着墙玩手机,没注意我就在电梯口。”
周筑愣了一下,没想起来相遇那一天更多的细节。
那一天,傅冬川例行公事地上班,在电梯里任人群淹没,一眼看见那个青蓝色乱发的人。
色彩太显眼了,像在跟所有人说,你们现在可以看着我。
我独特,笃定,值得被任何人留意至少一秒。
傅冬川随电梯一起上行,在会议室等待片刻,直到hr把这个人再度带到自己面前。
给予他更多的重用,在深夜带他去医院,然后放纵两个人的相互吸引,共处直到此刻。
如果幻觉都会褪色破碎,他只想永远都能看见他。
周筑忘了自己呼吸停了多久。
“你再说一遍?”
“你很真。”傅冬川如实地说:“也许我是在委婉地说,我对你一见钟情。”
周筑不说话了。
汽车穿过高架,两首歌陆续放完,他揭开纸盒,用小叉子吃那块彩虹奶油蛋糕。
傅冬川有条不紊地把车一路开到地库,见他渐渐吃完,伸手接纸盒壳子。
“垃圾给我。”
周筑不肯给:“我还在害羞。”
“又没说肉麻的话。”男人吻他手背:“我还没多咳嗽几声给你听。”
青年脸上发烫,起身去捂住傅冬川的嘴,又被亲到手心,更显得无措情迷。
“你是什么,勾人精吗?”青年哑声说:“傅冬川,这种话还不算在说爱我?”
“迟早会的。”傅冬川温声哄他:“再等等我。”
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又亲起来,亲了个没完没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里。
阿福刚刚和夜跑的邻居一起遛弯回来,形式性叫了两声表示欢迎,肚皮一翻呼呼大睡。
固定钥匙被扔到备用钥匙圈上,哗啦一声响。
周筑走路脚步不稳,被抱到餐桌上,撒着娇要和他一起练字。
墨汁淌得到处都是,沾得指尖掌心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