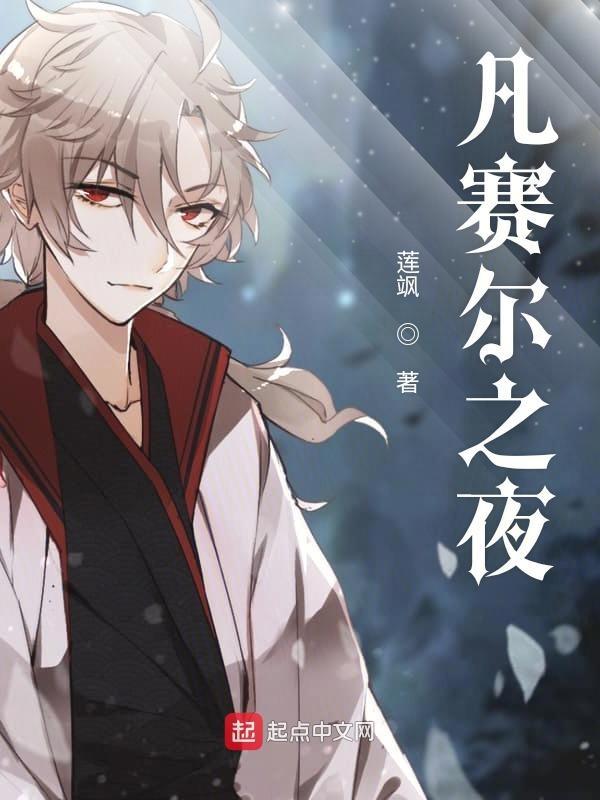乡村文学>男主霍砚女主明梨的 > 第1章(第1页)
第1章(第1页)
明徽刚睡下,就接到了丈夫霍砚深的电话。
“喂?”
沉沉黑夜,听筒里是另一个世界的喧嚣。
“老婆,我想你了。”
霍砚深明显带着醉意。
可尽管这样,明徽的心还是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
结婚两年,他从未这么亲昵地叫过她。
“砚。。。。。。”
话音未落,另一道声音盖过她,娇媚,缱眷,“砚深,我在这。。。。。。”
扬起的嘴角还未落下,她的心先坠到谷底。
明徽苦笑,原来是她自作多情。
想来也是,今天程玉的生日。
他连今天孩子的唐氏筛查都没陪她去,又怎么会在程玉的生日宴上想起她,想来只是醉了之后说胡话而已。
她确认事实如此,一颗心更加冷沉。
“喂?”程玉接电话,声音软糯,“明徽姐,砚深喝醉了,你来接他吧。”
说完,她又向霍砚深撒娇,“唱一个嘛,砚深哥~”
明徽攥着拳头,指甲掐进肉里,“太晚了,况且我肚子痛,我就不。。。。。。”
“明徽姐你说什么?”程玉笑,“我们在这等你,快来哦。”
“别。。。。。。”
话音未落,那边就挂了电话。
明徽坐在床上,摸着腹部,看向窗外。
大雪飘扬。
就算生下这个孩子,霍砚深会回心转意吗?
她心中迷惘,可该接他还是得接。
明徽无奈,在地库找了辆吉普。
今天冬至,家里保姆司机都放假,她又不会绑雪地链,只能找个看起来安全一点的车。
明徽心里惴惴,她半年前刚拿到驾照,开车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过来,何况这种恶劣天气。
幸亏路上空无一人,她小心翼翼开车,路上打了两次滑,但总算是有惊无险到了地方。
霍砚深还没出来。
明徽开了暖气,抚着肚子,头脑昏昏沉沉。
怀孕后,身体的不良反应开始显现,先是乏力嗜睡,再是腰酸背痛,似乎她对孕期反应更强烈一些。
想睡,却睡不安稳。
实在是精神折磨。
雪愈下愈大,几乎要盖住玻璃。
明徽等得心焦,又打过去电话。
响了两声,有人接了。
“喂,你们什么时候结束?”
“明徽姐,我们切蛋糕呢,你再等会儿吧。”
接电话的是霍砚深的兄弟,语气混不吝,看着台上喝彩,“亲一个,亲一个——”
她蠕蠕嘴唇,挂了电话。
算了,再等会儿,总归是待在车里,冻不着。
明徽这样想,她总是这样想,一遍又一遍地降低自己的底线,一遍一遍为自己***。
先是程玉,再是这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