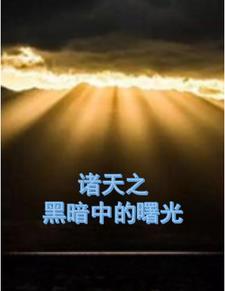乡村文学>那年秋天下雨了结局 > 第70章(第1页)
第70章(第1页)
金碧辉煌的电梯反射出人影,康耀明看着对面的自己,拨了拨头发,摸了摸别在裤带上的刀,酒
气熏天地冲了出去。水月厅里挤了十来个人,条纹状的海绵沙发上有人正在拼酒,还有人抱着话筒瞎吼,在者都是熟人,接二连三地和康耀明打招呼,廖锋坐在最里边的角落里,散落在桌面的扑克牌有细白的粉末,他似不知道有人进来,专心致志地用鼻子吸。康耀明在厚实的地毯上走了两步,一声大吼之后,拽了两只空的啤酒瓶就往最里面冲,带得玻璃钢上的拼盘酒水洒落一地,喧闹的室内霎时安静无比,惟有音响里还放着音乐。他在悠扬的奏乐下,扬起手中的酒瓶,丝毫不留余力地砸在廖锋的脑袋上,安静的空间立即充满此起彼伏地尖叫声。
有人过来拉架,反被他揍了一顿,举起只剩半个头的酒瓶威胁:“谁敢过来?他妈的有种试试!”这一声吼,吓得已经走到门边的女孩儿顿住了脚,低着头又默不作声地走了回去。
廖锋精神萎靡,像似陷在另一个空间里,结结实实挨了俩酒瓶子也不知道疼,就那么摇摇欲坠地挂在沙发上,松散了身体,仍由头顶上的酒流得满脸都是。康耀明最看不起他,不论何时何地,这个廖锋似乎永远都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他揪着他的衣领,把浑身不着力的男人提起来:“叫你出卖我!”一拳打在他的左脸,“连老子也敢卖了,老子最见不得背信弃义的人!他奶奶的那钱你他妈也没少拿!”拳打脚踢地发泄了一通,心底的委屈仍然无法缓解,他康耀明是敢作敢当的汉子,受不了平白无故的误会,杨振怎么能说他吸毒呢,这廖锋出卖他放贷就罢了,竟敢栽赃他吸毒。酒精已经达到麻痹大脑的最佳时刻,他心中有气,是被打的怨气,被冤的不服气,还有好兄弟反目的闷气,这时候终于找到宣泄口,没有任何顾虑,只想出这一口气。
廖锋已经被他打得鼻青脸肿,一副只剩半条命的样子,像小鸡仔似的毫无还手的意思。康耀明瞄到扑克牌上的粉末,一把抓过来就往廖锋嘴里倒,左手捏着他的下巴,迫使他张开嘴,接二连三灌了他四五张牌,又抓过酒杯继续给他灌:“栽赃老子吸毒!老子喂你,不是喜欢这玩意儿么,多吃点!”两三分钟之后,软趴趴的廖锋终于有了反应,却只是本能地挣扎了几下,他被呛着了,想咳的时候一直被康耀明捏着下巴灌东西,没咳出来,后来就没了声音。有女人已经开始小声地哭,缩在靠门的沙发上,紧成一团。最开始拉架的年轻人站在茶几前,看着歪倒在地的廖锋口吐白沫,颤惊着抹了一把冷汗,道:“他死了,你把他打死了。”
康耀明被酒精麻痹,听到死这个字时,才想起今天到这的目的,得意地笑了笑,他掏出腰间的刀,唰地戳进廖锋的小腹,鲜血迸溅出来,深色调的房间忽然变得诡秘骇人,汩汩鲜血沿着地毯缓缓外流,一直蔓延到k歌的显示屏下方,音响里还放着伴奏,缩成一团的女人终于吓得嚎啕大哭。廖锋睡在地上,脑袋还枕着半个沙发,嘴里的白沫混着黑血往外冒,眼睛上翻,身体不断地抖动。康耀明累得喘气,似心底的郁积终于解开,他睁着迷蒙的醉眼,拍了拍廖锋发冷发白的脸,似清醒似迷糊道:“我不弄死你,你就会弄死我,哥儿们谁叫你不识抬举呢!”
这晚,从不打烊的金煌不到十二点就把所有的客人撵了出去,到后半夜,整座建筑都被警察围了
个严实。
城里最人心惶惶的时候,杨振还在小浮桥的梅园里看雪,流动的小河被冰雪冻住,过了花期的腊梅也已经凋谢,零落的枯枝在风雪中微微颤栗。他看着夜灯下的树,想起小时候的苏颜,还有那时候如影子般跟在身后的六指,这么多年六指和他形影不离,相处的时间甚过身边的任何人。他不是不相信六指会爱上苏颜,只是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以前以为只要结果好,不管过程怎样,都不必在乎,事实上他曾经一直是那么做的,而现在,就这么毫无征兆地放弃爬得更高的机会,这感觉,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
他在亭子里坐了一会儿,将往起站的时候,忽然有人齐刷刷地冲进来。敛眉看过去,是五六个便衣警察,当即心下一顿,面上却是云淡风轻。那几个人和他熟识,慌慌张张跑进来,见他没有逃跑的意思,也收了警惕,不紧不慢地往里走。为首的人和杨振打过几次照面,放在衣袋里的手一直捏着枪,和他对视,先笑了一下:“出了点状况,恐怕你得和我们走一趟。”杨振开口,白雾在空气中散开:“什么状况?”
那人还笑,衣袋里的手已经握着枪柄:“去一趟就知道,具体情况上级清楚,我想只是例行检查
罢了,和往常一样。”
他也笑,淡淡地:“你让我走,总得给个理由。”
那人往前一步,一支枪便抵在杨振身前:“廖连胜的儿子廖锋你认识?”杨振想了想,皱眉,听他放低了声音继续说,“前半夜死在金煌,有人举报说是你的人干的,这还不是你下的令?”他的浓眉完全皱起来,身前想活捉他邀功的警长还在耳语,“这回的人不好惹,廖连胜多大的官儿,他能叫你好过?你还是乖乖跟我走,主动承认,这事儿还好商量。”
杨振约摸站了五六秒钟,抬手一个反掌就把抵在身前的枪送了出去,飞在半空中时走火的子弹还震天一声响,倒是把扳动开关的警长吓了一跳,半秒钟的功夫他已经跃身藏到亭子下的石柱子后,对方接连几发子弹都打中在刷了红漆的圆柱上,手下的人掏枪和警察对峙,连缓冲的功夫都没有,直接上膛开枪。他捏着手枪,粗糙的掌纹已经和那把枪磨合出了适宜的角度,在手下的庇护下翻墙跑了出去,岂料墙外是个陷进,成批穿警服的人正伫立在外等着他,幸好的是他们没有配备枪,不然就算他是个铁人,也会被打得满身窟窿,就那么徒手干了三四个人,闪烁着警灯的汽车忽然开始鸣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