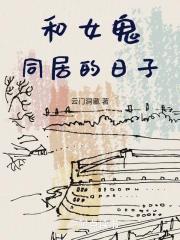乡村文学>万年孤单 > 第108章(第1页)
第108章(第1页)
神也会有愧疚。
阴君山一直保持沉默,心想她说的对啊,不过她漏了一点,就是……格林瑞德最想吞并的就是艾泽拉,做梦都想要,太阳王背叛了盟友,盟友反咬他一口,艾泽拉全面进军格林瑞德,血仇必血报。
阿蕊莉继续说,那天时间暂停后,她忘记了一切,又想起来了一切,可是没有记得叫阴君山的人,艾泽拉的胜利,铲除教会的胜利,属于她的胜利。
阴君山踏雪离开,封锁了阿蕊莉的记忆。
她去了东大陆,身着黑袍,头戴兜帽,走在长风渡的街上,今夜是扶桑节,她好像看到了之前的记忆,少女与少女,她与她们坐在一起吃鱼糕。
她走啊走,走到了街口,走到了古董店,不敢推门而入,走到婆婆那,看了一眼就离开了,走到图书馆,看到热热闹闹的景象,眼眶湿润了。
最后到了二十三重天,默默看了一眼许清柳,低声喊了一声扶桑,趴在案板上吃鱼糕的女人愣了一下,在抬头人已经不见了。
回到世界树,阴君山有些疲惫不堪。
好像一场死局也不错呢,她看到自己的白发,看到蓝眼睛,自己的血液融合了圣塞西莉亚的血液,变得越来越像她。
罗纳尔德日夜都会坐在世界树下,阴君山也坐过去,他们两个有一搭没一搭的讲话。
罗纳尔德说:“谢谢你。”
阴君山:“这比回溯之前好多了,回溯之前我是被动者,什么都不知道,在命运的长河中漂浮不定,回溯之后,我是带着阴谋去的,虽然老是在别人面前装头疼,装失忆,宿命也没有那么难打破。”
最后一句是她嘀咕着说的。
罗纳尔德笑笑,一只蝴蝶飞到他鼻头,亲吻一下,又飞到阴君山手心,这次她没有捏碎生灵,扬手送走了它。
飞吧,蝴蝶,突破命运的死局,飞向自由与天空。
一千年过去了,圣弥来到世界树前。
有些好笑,他会想什么。
阴君山走到他身后,听到了一句一句的话,岐年原谅我,对不起。
然后冷冷地说,岐年不会原谅你,从你把她害死的那一刻,她就再也不会原谅你,整个中州,整个世界,罗纳尔德,我,一切生灵都不会原谅。
圣弥没有哭,因为神不相信眼泪。
阴君山抱着梅林的木偶坐在世界树下,闭上眼睛,睡吧睡吧睡吧,一觉醒来就会好起来了。
突然有一天她醒来,还偷溜进了海沃德。
那里下起了红雨还有圣塞西莉亚的花瓣,斯嘉丽说,那是文德尔对自己的忏悔,圣塞西莉亚的自责。
阴君山有点怔愣,圣塞西莉亚死了,文德尔也死了。
又过了很久,一万年的牢期过去了,阴君山被放出来,与罗纳尔德打了声招呼,前往海沃德的死神之地,赫尔海姆。
有亡魂看到她的身影若隐若现,之后她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只有那只被遗弃在赫尔海姆的木偶,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她死了,她死了,她死了。”
她受够了万年孤寂,在世界树前,一遍一遍看梅林的轮回,一遍一遍测量自己的身高,它在缩矮,时间的反噬是痛苦的。
她悲痛,倒在一片圣塞西莉亚花海中。
我叫阴乔,是妈妈最爱的孩子。
我可以很骄傲的讲出这句话,妈妈很喜欢我,非常非常爱我,但爸爸很讨厌我,甚至厌恶我,想致我于死地。
在我接到父亲的第三百二十六封信的时候,对他的印象有些动容。
二楼有个在暗处的小房间,是父亲最喜欢的书房,他平常都会在书房写写东西,他写完总是有笑意。
父亲写了三百二十六封信,我问过,信要送到哪里,为什么要写,阳光下的金发男人勾唇笑得温柔,他说,是给你母亲。
每当提到母亲,父亲都是温和的。
他还说,母亲是个爱哭的孩子,会怀抱一束白色山茶花哭着说,梅林,你看,你怎么敢轻视我的爱。
我摩挲下巴,问:“母亲比父亲小吗?”
父亲放下笔,思考起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想好后弯唇笑意更浓,道:“嗯,晚山比我小几岁,”他像是想到美好的事情,提笔继续写。
那个时候,清风吹荡,阳光明媚,我看着父亲的笔尖充满爱意,感叹一声爱情的美好,最后,他放下笔,最后一封信写完后的一个月,消失了。
像是一阵浓雾,再也看不到人影,就连那一箱厚厚的信也一同不见了,我不是没有找过,而是找不到,一点踪迹都没有。
自父亲消失后,信又一封一封寄到家中,我按照寄信的地址回信,没有任何结果,现在新的一封信摆放在眼前,这也是最后的信,我颤抖着拿起,打开抖落出一张照片。
泛黄的边缘,相纸脆得仿佛一捏就碎,上面的女人抱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温柔的眸子溢出水珠,像是刚被欺负哭了一般,她很美,黄白灰的照片,因她有了色彩。
照片的背后是一小串数字0326,第三百二十六封信,是女人的生日,背面还写着女人的名字,阴君山。
我低低地笑出声,是母亲。
我将照片翻来覆去十几遍,最后在模糊不清的下角,写着年年岁岁,吾妻晚山。
晚山,是母亲的字,是父亲对她亲昵的爱称。
夜里我做了一个长梦,女人温热的体温怀抱住我,轻声道:“阿乔不要怕,母亲在,母亲保护你,母亲正抱着你。”
我无力地蹭蹭温暖,听到男人愤怒的声音袭来,是父亲的声音,他说:“阴乔,你先离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