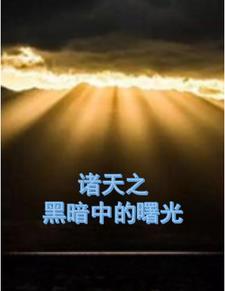乡村文学>无事岛屿 剧透 > 第11章(第1页)
第11章(第1页)
送她去举报之前,柏意说:“我知道你很想让他绳之以法,但是柏松根基太深,我们徐徐图之。”
周阳帆点点头,下了车。
现在看来,周阳帆做得很好。
柏意松了一口气,还没来得及放松,又想起什么似的,赶在王昱挂断之前交代了一句:“看好周阳帆。”
周阳帆自杀了。
来到医院时,看到王昱满脸愧疚,柏意有些无奈:“不是让你看好她了吗?”
王昱也不清楚,他接到保镖的电话时,周阳帆已经被送到医院了,据保镖描述,周阳帆整整一天没有下楼,他们觉得情况不对,这才发现周阳帆倒在了客厅,身旁是散落的不明药物。
病房里,周阳帆安静地躺着,神色安详,似乎睡得很香,长期的精神折磨使她看起来比正常女孩子更消瘦憔悴,经常让人忘记她也只是一个25岁的年轻女孩。
医生经过走廊时,看到柏意和王昱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站在一起,看起来实在危险,皱了皱眉,问他们是来探视谁的。
柏意面露担忧,指向病房内:“这是我妹妹,我们来照顾她的,医生,我妹妹她没事吧?”医生的目光看向柏意指的方向,又看了看手中的病历,摇摇头说:“没有事,血糖太低,营养不良,等她醒了观察一天,没事就出院吧。”
“不是自杀吗?”王昱探头。
医生挠头不解:“谁跟你们说是自杀,胃里干干净净的,饭都没吃,纯属饿晕的。不是我说你们,自己妹妹也不知道上心,已经这么瘦了,还不吃饭,你们都不知道吗?”
周阳帆这时候也醒了,医生示意柏意进去照顾,便接着查房了。
“你醒啦?”王昱又探头。
周阳帆看了看自己正在输的葡萄糖液,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很慢地眨了眨眼睛,说:“给你们添麻烦了。”王昱又说:“嗨呀,这有什么麻烦的,我还以为你自杀了呢。”
“自杀?”周阳帆也被这个说法整蒙了,然后笑着摇了摇头,“我才不会自杀呢,柏松进去了,我的好日子还在后边呢。”
王昱也傻乎乎地跟着乐呵:“对啊,你的福气在后头呢。”
看到周阳帆没什么事,柏意放下心来,让王昱留下照顾之后,自己开车去了看守所。
柏松看起来没受什么影响,隔着玻璃门,脸上是柏意一惯讨厌的傲慢神色,但柏意这会儿心情不错,坐在凳子上拿起听筒,问柏松狱里的生活怎么样。
“还不错,托你的福嘛,我的好侄子。”柏松看起来气定神闲。
柏意开门见山:“你知道是周阳帆,你也怀疑是我和她勾结,不是吗?难为你了,叔叔,还要在我面前强撑出不在意的样子。”
对面的人面色不动,仿佛柏意说的话跟他没有关系,柏意又接着说:“我是很想转型,但还不会把手伸到自家人身上,周阳帆也住院了,不知道是谁害的,话就说到这里了,叔叔,究竟是谁要把你拉下来,要看你自己心里怎么盘算了。”
一番话半真半假,柏松半信半疑,他沉默着,陷入了思考,他的小派系由利益组成,也能因为利益分崩离析,硬要从这些人中找出举报自己的,那每个人都有可能,他当然没有打消对柏意的怀疑,但他身在狱中,根本没有办法取证。
就在柏意准备离开时,柏松的态度终于转变,他喊住柏意,语气很小心:“想办法把我弄出去,我会给你想要的东西。”
柏意挥挥手,留给柏松一个背影。
剧组里今天喜气洋洋,于墨的女朋友今天来探班,两个人在大家八卦的追问下,承认马上要订婚了,安陆一向不太爱凑热闹的人,听着大家起哄,也忍不住跟着笑。
他认为自己一向离幸福很远,也很难拥有,但看到别人幸福,也还是会感到与有荣焉。
“她刚开始说什么也不跟我在一起,说我们两个差距大,可是总要试试的吧,我只知道没有她,我会很遗憾。”于墨开始讲自己的恋爱史,剧组的小年轻们都“哇”着捧场。
杜迪程嚷嚷着要让小两口请吃饭,于墨一口答应,喊着大家开开心心上车,安陆想了想,没有去:“你们先去吧,我再等等。”
等谁呢,安陆不愿承认也不愿细想。
于是组里就只剩安陆一个人了,他慢吞吞地把设备搬在一起,又慢吞吞地擦拭道具,但就是不装进箱子里。
然后一双手伸了过来,木香淡淡地闯进安陆的感官,再然后是熟悉的欠揍声音,安陆偏头,看到很润的玉牌。
“安导是不是没我不行呀,这么多东西肯定搬不完。”
“嗯。”
没你不行或是搬不完。
柏意没想到安陆是这个反应,“嗯”是什么意思,一个字可以引申为许多意思,柏意不敢问下去。
风很慢的停了,破旧的厂房外边是大片的荒草地,月亮还没升起,草地被吹动的波澜缓缓停息。
安陆看着柏意把设备装好,然后说:“他们去吃饭了,我没去。”
“在等我吗?”
但安陆又不说话了,柏意有些紧张,又问:“那,要一起吃晚饭吗?”
又起风了,安陆的刘海长了不少,在额前微微动着,有些刺到眼睛,柏意被安陆看着,伸手把那些碎发撩到旁边,安陆的睫毛很脆弱的颤了一下,说:“那就一起吧。”
其实深夜的街头没什么好吃的,过去了热闹的时间,路上就只剩下月亮做伴,两个人更像是散步,巷子不宽,两个男人并排走就很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