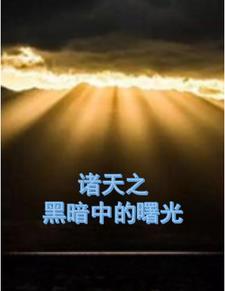乡村文学>大广苑原著叫什么 > 第55章(第1页)
第55章(第1页)
杨宜简迟疑片刻,终于接过笔来,饱蘸浓墨开始奋笔疾书。
他写一页,陆坦看一页,看完便丢进脚踏旁的火盆里焚毁,约莫一炷香的时间,杨探花才放下了笔。
见对面的郎君烧掉最后一页后脸色凝重眉头紧锁,杨先生轻声道,“阔然自幼心胸旷达,遇事向来不喜自寻烦恼,可这件事上,宁可远走他乡也不做佞臣,足见心中另有一片河山。”
陆坦喃喃道,“学生粗鄙,并无先生所言的「大义」,只是不愿为虎作伥…”
“不尽然,”杨探花拦下了他的妄自菲薄,“那片河山想必是用来兼济苍生的。”
这题目就扩展得有点大了,陆坦扪心自问,他的目的,或者说志向,是否真得如杨先生所说得那般高远。
他不过是个衣食无忧的大家公子,厌倦诡谲多变的朝堂,疏于打点人际关系,讨厌昧着良心做事,只想当个无拘无束的泥腿子。家国天下这些祖辈津津乐道的宏图大志,对他而言如同镜花水月,不够写实。
如今情愿跑这一趟,也是打着忠君的旗号免于受制于人,如此说来,说「兼济苍生」也不为过,顺便。
一旦某个平庸的梦想忽然被拔高到了某种超然物外的高度,当事人的第一反应往往会是不自信,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稳住局面掌好舵,想到此,陆坦不禁问道,“先生为何选我?”
论资历论背景,择一权臣或内阁老臣更有胜算,现成的就有当朝大儒岑老大人。
仿佛早就料到阔然会有此一问,杨先生不疾不徐道,“因为杨某跟陆大人一样,不愿拖累他人殃及无辜。大人手持敕走马银章,没准还有尚方天子剑,趋避得法,颇有胜算。更重要的是…大人不会对秦家小姐不利。”
此时秦家小姐已将一根软烂入味的肋排啃得干干净净,扔进骨碟发出叮当一声脆响,吮了吮指尖才算心满意足。秋葵端起炉灶上温着的水壶给她家小姐净手,秦宁瞥了一眼紧闭的东厢房门,问道,“杨叔进去几时了?”
不等秋葵答话,蹲在窗棂边埋首吃得津津有味的陆不急闷声道,“快一个时辰了。”
这位仁兄,大快朵颐之余倒没忘了当差。秦宁稍加思索,吩咐秋葵道,“再去给我端一碗肉。”
秋葵原地没动,蹙眉道,“好吃小姐也明日再吃吧,莫要积食了。”
秦大小姐摇了摇头,低声道,“那两位闭门半晌,定然不是闲聊,等他们出来,本小姐说不定就有事儿干了…”
然而等东厢房的门一开一合,两位谦谦君子作揖拜别,直到夜幕低垂,也没见有什么事儿能给秦遇安干。冬葵顺着经脉给她捋着胳膊,帮她消食,秦宁眉头拧成疙瘩,怎么想怎么不对劲,陆坦不可能这么消停。
杨宜简的探花之名实至名归,此君心思缜密,屈居大广苑当账房先生实属大材小用。小陆郎君如此记挂杨先生,必然是心有所想,搞不好是有事正好需要杨叔出谋划策。
送亲队伍已经在青龙州休整了两天,后日便要启程继续北上,若在这一站有事情没办,错过了今日,拖到明日未免仓促了些。
胡思乱想过甚,不知不觉已到了亥时,秦遇安仍毫无困意,正举棋不定抽那本书出来打发无眠,庭院内忽然一阵大乱。
短兵相接吵吵嚷嚷,在宵禁后宁静的夜晚格外喧嚣,秦宁愕然,“又有刺客?”想不到她这个假公主挺遭人惦记,行情还不错。
但见冬葵裹一身寒气推门而入,进门不问安也不好好说话,掌心不离刀柄,死死盯着秦遇安的眸子道,“你,是我家小姐还是妖孽?!”
语气之凌厉仿佛秦宁已然被夺去了魂魄成了妖魔。秋葵登时冲上去横在了冬葵的刀前,“成天这个毒那个毒的乱扔,今日是药着自己了?怎么说起胡话来了!”
冬葵三魂回了两魂,还刀入鞘道,“小姐身居驿馆有所不知,青龙州的大街小巷已经疯传半个时辰了,不止一户人家看到了赤狐现身,纷纷疑心是不是押在城中那座塔里的赤狐仙又冲破封印跑出来了…”
不等秦宁,秋葵直说荒谬,“什么赤狐白狐在咱们苑子里见得还少么,怎么单就它能得道成仙了?”
“可说呢,”秦宁笑盈盈道,“是吸了多少男子的阳气才修炼成的?”
“不是,要是狐媚子勾引男子也不新鲜,”冬葵将听来的奇谈怪论一一说给秦遇安,“这狐仙专门附身在娇弱女子体内,寻着机会去接近身怀六甲的娘子,乘其不备!吸了那腹中胎儿的纯阳之气~”
秦宁倒吸了一口冷气,“之后呢?胎死腹中了?”
冬葵摇头,“大多倒也没有,七八个月大的小娃娃已然成型了,只是精疲力竭这胎便坐不稳,瓜不熟就落了地,各个先天不足身体羸弱。”
所以方才该是有人看到赤狐翻墙进了秦遇安的院子,玉安公主正好是一妙龄女子,冬葵担心她被狐仙附体。
这就有些离奇了,秦遇安不禁锁眉道,“既然这赤狐害人不浅,为何不将其斩草除根?”
“万万不可,”冬葵摇头道,“据这皓月玲珑佛塔的主持道真长老所说,狐仙身上聚着成团的小儿真气,若轻易斩杀,唯恐对那些孩童不利,只能将其活捉封印在那玲珑塔里…”
秦遇安挑眉抿了下唇,“然后它就刚好在本小姐路过的这三天里跑出来了,还碰巧跑进了我的院子里?”
冬葵光想着保护我方大小姐,我管它是意外还是巧合。听秦宁如此一问,被妖魔鬼怪祸乱的脑仁儿冷却下来三分。

![[原神]要来杯蜜雪冰史莱姆吗](/img/5775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