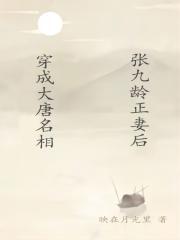乡村文学>你不告而别的那些冬天全文免费阅读 > 第82章(第1页)
第82章(第1页)
猝不及防,杨今的睫毛眨了眨,他的睫毛刮在围巾上。随后是一股烟草味,是梁也的手伸过来,帮他仔细整理好,工整地围在他脖子上。
杨今把脸埋进围巾里,吸了一大口围巾上的烟草味,不再说痒了。
“车给小工进货去了,今天走路回家。”
“好。”
杨今其实也很喜欢走路,冬天和梁也并肩行走,可以趁无人的时候把手放进梁也口袋,有人经过又拿出来,然后就可以等着被梁也强行拽进去,揣好。
梁也问:“你俩刚才说什么了?”
“文静以为我要去澳门,我告诉她我不会去的,我会和你待在哈尔滨。”杨今犹豫片刻,“她还问起你妈妈会不会反对,我没回答她,但我觉得……阿姨是一个很好的人,总有一天她一定会理解的,以后我们一起照顾她,好吗?”
不下雪的时候,冬天是嘈杂的,马路上的车流声、小孩儿跑过时发出的玩闹声,甚至是环卫工人扫帚擦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
世界入耳,唯独身边的人如此安静。
杨今已经许久没有在梁也这里感受到不安,某种直觉驱使他抬起头,仔细看梁也的表情。可是梁也总是没有表情,他浅浅蹙着的眉也说明不了任何。
很久之后,梁也终于回他:“好。”
——大抵也不算很久,只是杨今觉得久。因为他以为这是不用考虑就能回答的事情。杨今以为谈恋爱就是一辈子,一辈子就是成为家人。
曾经他们拉扯过无数次的死胡同就在跟前,杨今伸手拉了拉梁也的衣服,抬眼看他。
梁也垂眼与他对视片刻,会了意,勾着他肩膀把他带了进去。
走到死胡同最深处,刚停下脚步,杨今就急切地说:“梁也,我不会去澳门的。”
他贴近梁也,手抓紧他腰侧的衣服,不遗余力地向他剖白:“你让我留在哈尔滨,我说了会留下,就一定会留下的。”
梁也深深看着他,眼神比最深的夜还要深。杨今总觉得他今天有哪里不对,却又说不出具体是哪里。
那只因为他受伤的左手抚上他的侧脸,梁也声音低沉:“怎么突然说这个。”
“我总觉得你没有真的信过我。”杨今失落地垂眸,“你是不是在得过且过,跟我谈对象,谈一天是一天?”
杨今又抬起眼,祈求他的信任:“我还在学葡语那是为了糊弄我爸爸,我都算过了,我妈妈预产期就在高考前不久,那会儿他们一定没有心思管我……你别不信我,好吗?”
北风灌入死胡同,杨今不可救药地想起他和梁也刚认识时,梁也在这里对他说过的话。
梁也说,你这么好的条件,别往歪门邪道上走。梁也说,我不是同性恋。
最憎恶的不确定感与灌入胡同的北风一同袭来,吹刮在杨今的脸上。
他回头看了一眼胡同口——没人,然后急切地靠近梁也,手环在他脖子上,祈求他的回答。
“我信你。”梁也终于回答他,手放在他的腰后,让他不要抱得太吃力。梁也顿了顿,“我只是——”
“只是什么?”杨今追问。
梁也沉默很久,不知道在想什么。后来他说:“只是觉得自己赚钱太慢,担心给不了你太好的生活,我家条件本来就不好。”梁也顿了顿,“……很不好。”
杨今从未觉得梁也家哪里不好,他刚想要追问梁也为何这么说,梁也就低头吻了上来。
无人的胡同里,不下雪的冬夜,一个温暖又深刻的吻发生在初次体味爱情的时刻,总是会让年轻的灵魂忘记上一秒他还在触碰梁也的痛苦。
他几乎就要接近痛苦的真相。几乎。
---
那天之后,梁也又忙碌起来。
梁也说临近年关总是比较忙,一方面是要多进一些年货,另一方面学生放假,来店里看电影的人多了很多,小工晚上一个人忙不过来。
有理有据,杨今自然没有任何怀疑。
某天夜里,杨今送走葡语老师,葡语老师问他是不是已经向澳门的大学递交了申请,截止日期就在最近。
杨今说已经递交了,其实没有。
几天后,杨今接到了杨天勤的电话。
他家的电话是柳枝桂离开不久后装上的,即使是在哈尔滨最有钱的友谊小区,也是一件非常打眼的事情。
电话里,杨天勤要他抓紧时间准备澳门学校的申请,杨今如往常一样应付着,谎称自己已经递交。
又过了几天,杨今再次收到杨天勤的电话。
“你就马上来澳门一趟,家里有要紧的事情,马上买票,后天一早我必须看到你。通关手续已经托人给你加急办好。”杨天勤说完就挂了电话。
杨今握着电话听筒没有放下,他闭上眼睛,命令自己立刻冷静下来。
他在原地安静地思考了一分钟,当机立断,马上把哈尔滨这个家里所有钱和值钱的东西都装好,全都拿到梁也的店里。
时间不多,杨今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梁也骑车一路狂奔,送他去车站。
路上,梁也问他:“你爸怎么忽然要你去?”
梁也总是稳定,可是问这句话时,杨今头一次听到了他的不安。
前几天刚刚在死胡同里对梁也说不会去澳门,今天就急匆匆启程。他这么快就食言了。
哈尔滨火车站前巨大的塔钟敲响,正点,钟声弥漫在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们耳里。是夜,是北风吹飞他们身上的大衣,正好给他们的告别吻打了掩护。
“梁也,我会回来的。”杨今笃定地对梁也说,并且望向他的眼,“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