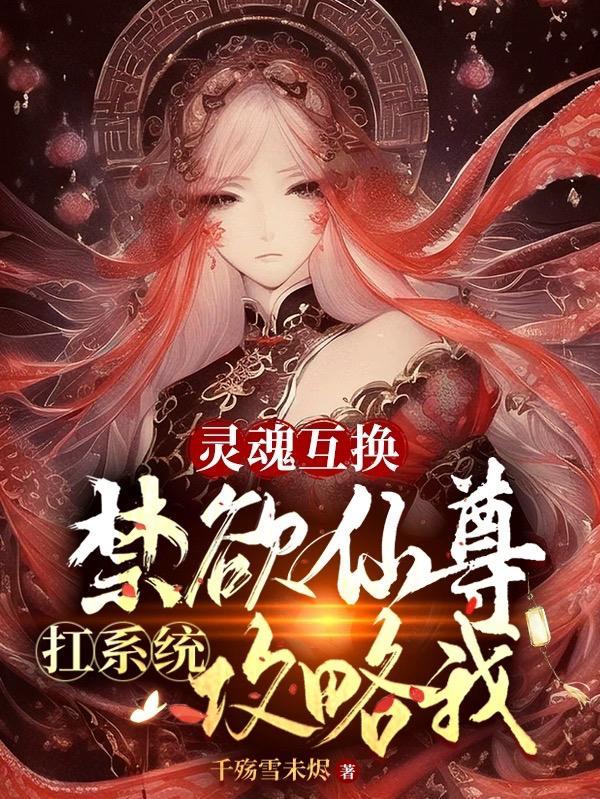乡村文学>万华镜4 > 第六章 一次虚荣(第1页)
第六章 一次虚荣(第1页)
沈方说要乘轨道车离开,家住的地方有些远,没有让张宇安送自己。
车站开往工业区,根本没有能住的地方,前往站点的都是换夜班的工人,但张宇安没有说什么,告别后便离开了。而沈方也正如他所料,在二十分钟后拖着大包行李,艰难地靠在电梯边又爬了上来,硕大汗珠滑过脸庞,一闪身拐入还没通上夜灯的街道。
这是沈方第一次虚荣,残废的身体毫无需要珍惜的价值,所以连走夜路都是大摇大摆的,不会有人觊觎自己的身体或是随身携带的财物,然而张宇安的出现让沈方开始想要珍视自己的生命,祂在注视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肯定。
沈方其实不需要富人施舍自己金钱或是怜悯,钱可以自己赚,伤心久了也不必安慰,但张宇安只是因为音乐找上了自己,两个享受音乐的人平等的交流,这才是自己一直需要的事情,抛去高高在上的慈悲,沈方并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卑微。
祂越想越激动,苍白的面孔多了几分的红润,可随后一声刺耳的招呼迎面泼了冷水,坐在廉价合租公寓门口的房主是位身材厚实的老太太,搬了一个藤椅,正在指使儿子往外搬家具,瘦弱的母亲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在沉默中强忍颤抖,放弃了哀求。
这是几乎每过几周都要上演的剧情,公寓里住的都是最边缘的人物,像沈方这样的还算少部分,更多的是单
身母亲带着一两个孩子,从事最廉价的清洗缝补和制作食物的工作,至于孩子的父亲往往死于药剂厂。
随云脑系统产生的三种药剂,用于清洗记忆的红色VIR,保护记忆的蓝色BIA,还有模糊记忆的黄色ACH,都需要古代那些自诩神明的人工智能遗留下的机器制作出的核心化合物,断层的现代科技至今无法解开古代的科技黑箱,而以云脑为核心的社会机制对于这三种药剂的需求又是必要的,于是剥削最底层之人生命的体系完美重生,所有人都在演戏,维护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再熟悉不过的新秩序。
那些死于化合物排放出的有毒气体的工人通常是埋在工厂西侧的农地,家境好点的还会加个木制盒子,在工作中倒下的人直接被拉到工厂东侧的公寓,引发短暂的骚动,找定去世者的家人后,妻子会哭着跑出来,紧跟着的是还不懂事的小孩,若还有大点的孩子则会出现在最后面,伏在门边躲避上方的视线。
难得的娱乐节目随即开始,大伙一起看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哭,闹了一阵后又会有人把尸体往西边拖回去,但节目这才进行了一半,接下来失去丈夫的妻子还有继续找出路,要么和丈夫一样用命换钱,要么用尊严换钱,或者像今天的这位母亲一样,拼了命地工作维持现状,然后挨上孩子生了病,最后脆弱的支柱啪嗒一声折断
了,孩子向母亲不停地抱歉自己生病了,稚嫩的童声突破了女人最后的防线,在失声的呜咽中勉强挤出话来安慰孩子没有事。
沈方回来时赶上的正是娱乐节目的最高潮,大家都在等着女人做出最后的选择,若是代替丈夫上工,一帮热心的“军师”便会凑上来提醒她在工厂的规矩和偷懒技巧,若是放下最后的尊严,另一帮贴心的“救世主”就会从门口涌出来施舍些小破布。
若是女人拖着仅剩的行李带孩子流浪,公寓就更热闹了,人们猜测着女人最后的下场,并怀着最诚恳的善良祈祷孩子能有“高升”的机会,若是这孩子确有几分姿色,能显出灵气,那就要拿曾经的几个“状元”出来说事了,说是失去父母流浪在大街上的某某小孩被捡回去当侍童来改变命运。
没有人会去可怜他们,这些人都是“罪人”的后代,而所谓“罪人”则是在古代选择服从人工智能,没有跟随军队反抗的“懦夫”,消灭了人工智能后,仇恨愤怒自然要由这些人承担,也算是上天保佑,重启的人类文明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一个庞大的,合乎情理的奴隶群体。至于沈方这种从“上边”落下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毕竟现在的审美传统还是和一二十年一样,崇尚力量的同时倾轧缺憾。
沈方看着熟悉的一幕,攥紧口袋里赚来的钱,手心开始冒汗,浸得口袋潮潮的
。
“春姐,她欠了多少钱啊?”
踌躇间,沈方又想起了今晚与张宇安在月光下的共舞,莫名给了祂一种想要从麻木中挣脱出来的勇气,善良总是需要实力来支撑的,而幸运也是自己实力的一部分,今晚靠着幸运多赚了一些钱,于是好像有了那么一点支撑善良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