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学>美女开车遇到碰瓷的电视剧 > 第237章(第1页)
第237章(第1页)
并非酒楼不好,而是厅堂中坐满了男子,就算知道可以去雅间,但看着他们哄闹的样子,依然没有踏足的欲望。
她独自走了好一会儿,终于瞥见一家酒楼不太一样。
三层的小楼精致气派,栏杆上的新漆光滑锃亮,灯火明亮夺目,照得人心头都亮堂起来。
最关键的是,厅堂中七八成皆是女客,偶有男子也是温声细语,彬彬有礼。
林知雀越看越熟悉,忽而想起来她似乎来过,正是殷惠儿与陈陵远一同打理地那一家。
至于他们所作的营生她算是亲眼目睹过,心里有数。
思及那日伺候宾客的俊俏少年,林知雀避讳地错开目光,迟疑地伫立在门前,不知是否应该进去。
这种地方她本不该来,今日纯属机缘巧合,况且她虽然与那家伙闹别扭,却完全未到背弃婚姻的地步。
可是她打量四周,这家酒楼是最合心意的,双腿也酸软发胀,不愿再往远处走了。
林知雀纠结地攥着袖口,望着敞亮的大门,终于下定决心,闷头踏上了台阶。
她洁身自好,行得正坐得直,只是来找熟人朋友喝酒,这有什么要紧?
再说了,那家伙不也在统领府听歌伎弹琴唱曲么?难道她就不行吗?
想到这些,林知雀豁然开朗,本就不多的负罪感消失殆尽,大方行至酒楼前台,问道:
“殷姑娘在吗?陈大哥呢?”
负责收银的是位年轻姑娘,生得伶俐讨喜,一刻不怠慢,笑吟吟地答道:
“哎呦,您找咱们掌柜呀?真是不巧,他们今日出门采买,估摸再晚些才能回来。”
听罢,林知雀失落地应了一声,转身便要离开。
那姑娘机灵地上下打量,见她衣衫低调简朴,却是金陵上好的云锦,发髻上的攒珠钗熠熠生辉,想必身份不凡,立刻话头一转,出声唤道:
“夫人且慢!”
待到林知雀不解地回头,那姑娘笑得热切殷勤,拉着她回到店内,诚恳道:
“其实掌柜在不在是一样的,咱们有的是好酒水,还请夫人上座。”
说着,她恭敬地伸长手臂,压低了腰身,请她走上楼梯去雅间。
事已至此,林知雀不好拒绝,更何况起初就想找个地方歇脚而已,欣然颔首答应,随着她的引导踏入宽敞干净的阁楼。
侍从瞥见那姑娘的眼神暗示,纷纷谦恭地行礼问安,手脚麻利地端来酒菜,默默退了出去,给她留下自由的空间。
那姑娘请林知雀慢用后,登时脚步匆匆地走下楼梯,环视堂后的一众少年,朝着最纯澈俊俏的一位招手,命令般道:
“小九,你过来。”
少年蓦然抬眸,瓷白细腻的脸庞光滑柔嫩,比姑娘家还要楚楚动人,乖顺地“哎”了一声,姿态翩然地走到那姑娘身边,静待她的安排。
“阁楼有位贵客,不仅与掌柜相识,还瞧着大有来头,你去好好伺候。”
那姑娘低声叮嘱一番,随即把脸一沉,温和的面容瞬间变得严厉,一字一句道:
“务必哄她开心,若是惹她不高兴了,你今日一文钱也拿不着!”
少年被她的脸色吓了一跳,惊疑不定地点头,紧张地咬着唇瓣,跟在她身后去了阁楼。
彼时,林知雀刚刚坐定,用了些饭菜垫饥,口干舌燥地险些噎住,顺手拿起斟满的酒盏,犹豫一下后终究放回原位,灌下一盏茶润喉。
她很清楚自己的酒量,光是闻着酒香都有些迷醉,这一杯下去定会找不着北,让人看笑话。
就在这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方才的姑娘探出脑袋,笑得意味深长,一把扯出身后的少年,毫不留情地推进来,一副请她慢用的模样。
林知雀顿时明白是什么意思,连忙慌张地摆手拒绝,道德和教养都无法接受,拼命挥手让他们离开。
那姑娘只当她是羞怯和客气,愈发不肯带少年回去,愁眉苦脸道:
“夫人您是贵客,如果招待不周,掌柜会责罚我们的,求您开恩收下吧!”
话说到这份上,那姑娘身子压得更低了,只差跪下恳求,好似她不收留就是为难人似的。
林知雀耳根子软,曾经又历经变故,知道寄人篱下的苦楚,一听他们可能因此受罚,心里并不好受,面容泛上几丝踌躇。
那姑娘趁此良机,眼疾手快地将少年塞进去,反手关上房门,三两步冲下楼梯,不给她反悔和推拒的机会。
林知雀还没来得及说话,就愣怔地伫立屋内,与少年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坐回原本的位置上。
她瞥了少年一眼,约莫才十六七岁,生得唇红齿白,相貌堂堂,俊俏眉眼微微上扬,眸光却带着懵懂无措,如同初来人世的小狐狸,试探着讨好人类。
这一刻,她想起话本上的故事,忽而觉得也不能怪纣王,以及有些郎君为何会流连烟花之地。
可惜她是有夫之妇,虽然夫君是个狗东西,但她自幼恪守礼节,绝不会行不轨之事。
林知雀轻咳一声,与少年保持距离,淡漠道:
“你该干嘛干嘛,不必理会我。”
少年意外地睁大双眸,第一回有客人对他不为所动,略显失落地打量自己,挫败地点头应声。
他依然惦记着那姑娘的话,生怕行差踏错拿不到银子,一整天都白干,硬着头皮挪近一些,坐在这位贵客几步之遥的地方,纤长手指置于古琴之上。
琴弦颤动,身姿随着韵律轻微摇晃,每一缕发丝都赏心悦目,好似一幅耐看的美人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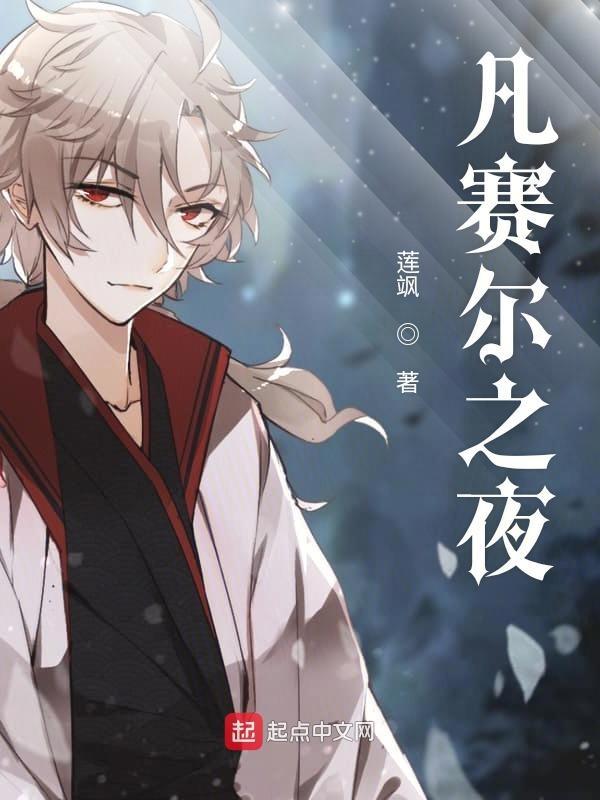

![大佬总勾我撩他[快穿]](/img/1497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