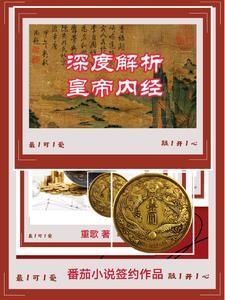乡村文学>沙丘 1 > 03(第2页)
03(第2页)
杰西卡转过身,看着窗外越来越浓的夜色:“那个叫厄拉科斯的星球,真有那么糟吗?”
“够糟的了,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我们的护使团已经去过那儿了,多多少少使局势缓和了些。”圣母站起身来,抻平衣袍上的一处褶痕,“把那小男孩叫进来。我得马上走了。”
“非走不可吗?”
老妇人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杰西卡,孩子,我真希望我能替代你,替你承受痛苦。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走自己的路。”
“我明白。”
“我爱你,跟爱我的亲生女儿一样,但我决不能让这种爱妨碍我们应尽的职责。”
“我明白……这是必要的。”
“你做过什么,杰西卡,为什么那么做——这些你我都清楚。但出于好意,我不得不告诉你:你家这孩子成为贝尼·杰瑟里特至尊的可能性很小。千万不要期望过高。”
杰西卡生气地抹掉眼角的泪水:“您又使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女孩了——正在背诵着第一篇课文。”她咬紧牙关,一字一顿地说:“‘人类决不能屈服于兽性。’”接着,杰西卡哽咽一声,顿了顿,又低声说道:“我一直觉得孤独。”
“这也是考验之一呀。”老妇人说,“人类几乎总是孤独的。现在,去叫那男孩吧。对他来说,这一天一定很长、很恐怖,但给他的时间已经足够了,够他思考并记住这一切。我必须再问几个有关他那些梦的问题。”
杰西卡点点头,走到冥想室,打开门:“保罗,请你来一下。”
保罗故意磨磨蹭蹭地走出来。他瞪着母亲,就好像她是个陌生人。看到圣母时,他的目光中流露出警惕的神情,但这次他朝圣母点了点头,就像是在和一个与他身份地位完全相同的人打招呼。他听到母亲在他身后关上了房门。
“年轻人。”老妇人说,“咱们来回顾一下你做过的那些梦吧。”
“你想问什么?”
“你每晚都做梦吗?”
“并非所有的梦都值得记住。我可以记住每一个梦,但有些值得记,有些不值得。”
“你怎么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我就是知道。”
老妇人瞥了一下杰西卡,又把目光转回保罗身上:“你昨晚做过什么梦?值得记住吗?”
“是的。”保罗闭上双眼,“我梦见一个洞穴……还有水……那里还有一个女孩——她很瘦,长着一双大眼睛。她的眼睛全部是蓝色,没有一点儿眼白。我跟她说话,把你的事告诉她。我告诉她,我在卡拉丹看见了圣母。”保罗睁开眼睛。
“你告诉那个陌生女孩,说你见过我,那你昨晚告诉她的岂不是今天发生的这些事?”
保罗想了想,然后说:“对。我告诉她你来了,而且在我身上留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印记。”
“不可思议的印记。”老妇人吸了一口气,向杰西卡投去一瞥,接着又把注意力转向保罗,“现在,老实告诉我,你在梦里看到的事是否经常会真的发生?一如你梦中所见?”
“是的。我以前也梦见过那女孩。”
“哦?你认识她?”
“我会认识她的。”
“给我讲讲她。”
保罗又闭上眼睛:“我们在岩石丛中某个很小的隐蔽处。天已经快黑了,但还是很热。从石缝间可以看见连绵起伏的沙丘。我们在……在等待……好像是要等着与一些人会合。她害怕了,但竭力掩饰,而我却很兴奋。然后她说:‘给我讲讲你家乡的水吧,友索。’”保罗睁开眼:“很奇怪,我的家乡在卡拉丹,我从没听说有哪个星球叫友索。”
“还梦见别的什么了吗?”杰西卡迅速问道。
“是的。或许她是管我叫友索。”保罗说,“我也是刚想到的。”他再次闭上眼睛:“她让我给她讲水的故事。于是我握着她的手,说要给她背一首诗,然后我就开始背诗。但我还得不时向她解释诗中的语句——像海滩、浪花、海草和海鸥什么的。”
“什么诗?”圣母问。
保罗睁开眼睛:“哥尼·哈莱克写的那些伤感小诗中的一首。”
保罗身后的杰西卡背诵起来:
我记得海滩上的篝火那带着咸味的轻烟,
松林里阴翳连绵——
屹然矗立的林木,
全都那么坚挺、整洁——